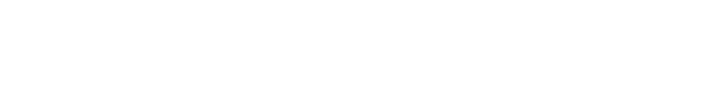罗丰 曹中俊|甘肃武威慕容智墓中的胡瓶与葡萄酒
甘肃武威慕容智墓中的胡瓶与葡萄酒
罗 丰 曹中俊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丝绸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
摘要:2019年9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现了武周吐谷浑喜王慕容智墓,这是目前考古发现中唯一保存完整的吐谷浑王族墓葬,墓中出土器物800余件(组)。本文以墓中出土的素面银胡瓶为主要讨论对象,通过多重对比,推测其为粟特型胡瓶,其制作工艺与中亚金银器有着渊源关系。瓶中所盛204克葡萄酒是目前国内所见最早的白葡萄酒实物遗存,为探讨胡瓶功用及葡萄酒东传问题提供了重要资料。此外,墓葬还显示出鲜卑文化、吐谷浑文化、北方草原文化及汉文化等元素。可见,凉州乃至河西地区在中古时期东西文化交流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多元文明的交汇之地。
关键词:吐谷浑;粟特文化因素;青海道;胡瓶;白葡萄酒;文明交融
2019年9月,考古工作人员在甘肃武威天祝藏族自治县发现了一座古墓葬,随后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牵头对其进行了发掘[1]。根据出土的《大周故慕容府君墓志》可知,墓主即吐谷浑喜王慕容智[2]。慕容智是慕容诺曷钵的第三子,其母正是唐朝的弘化公主。吐谷浑被吐蕃灭国后,其王慕容诺曷钵(635-688年在位)携弘化公主及残部逃至凉州武威时,生于永徽元年(650年)的慕容智也跟随父母一同前往。最终于天授二年(691年)三月病逝于灵州,同年九月,其后人将慕容智“迁葬于大可汗陵”[3]。慕容智终官为“守左玉钤卫大将军”,正三品,其墓葬规格大致与唐朝三品官员墓葬相符。
墓中出土器物众多,主要分布在墓室和棺椁内,包括陶器、漆木器、金属器、石制品、革制品及丝织品等共800余件(组)。其中不乏诸多精美者。当前学界针对慕容智墓的选址与葬俗、出土墓志、彩绘陶俑、壁画颜料等已进行了相关研究[4]。墓中除了随葬中原唐朝风格的器物,还有不少蕴含外来文化因素的器物,如戴尖帽着胡服的胡人俑、金蹀躞带(其中铊尾饰有胡腾舞者)、胡禄、鸣镝箭、胡床、黄地大象纹锦荒帷及各式异域风格织锦、铁甲胄、银胡瓶、鎏金银饰片、金质下颌托等。透过这些器物可发现,墓葬中蕴含有较多粟特文化因素,或因吐谷浑与粟特有着深入交流和交往。尤其是盛有白葡萄酒的胡瓶,为考古工作中首次发现胡瓶功用的力证,格外引人注目。
本文以墓中出土的胡瓶及白葡萄酒为契机,对该盛酒胡瓶的形制风格、制作工艺、功用及其所反映的葡萄酒东传等问题进行探讨。
一、慕容智墓中粟特型胡瓶的推断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清理吐谷浑喜王慕容智墓时发现一银胡瓶(G:12,图一、图二)。胡瓶通高39.5,口长12、口宽1.8-5.6、底径10厘米[5],重1.3千克,容积约6升。鸭嘴状流,粗短颈,腹部圆鼓,方形实心单柄,高圈足座。兹将其细节描述如下。
银瓶口沿 该银瓶出土时瓶口用黄色布包封,内有封泥和木塞残渣。与大多数胡瓶一样,也有一鸭嘴状的流,俯视时呈扁桃形,上圆下尖,长径12、短径最宽处5.6厘米,敞口,圆唇,侧视时可见0.2厘米的窄边。
银瓶颈部 颈部较粗短,上细下渐大,颈部长约8.7厘米。
银瓶腹部 腹部上细下逐渐加大呈圆鼓状,然后内收,呈圜底,再与圈足相连,最大径在腹上部,约26厘米。口沿下方到腹部下端有一长达20厘米经合焊后相连的痕迹。基体表面打磨后抛光,胡瓶整体素面无纹。外壁有明显的捶揲、烟炱和使用痕迹。
银瓶圈足 圈足中空,呈喇叭形,上敛下撇。高7.75厘米,底径10厘米。圈足底部内侧刻有数字,其中“观”和“十”字最为明显,疑似还有“贞”字。
银瓶把手 把手方形实心,上端焊在银瓶口缘部,下端焊在银瓶的中腹部,下端与腹部焊合处呈桃形,中心有一稍凸起的圆形铆钉。把的上端和口缘相接处饰一圆珠,其直径约1.8厘米。
从目前所知文献来看,早在三国西晋时期胡瓶已传入中土,其早期多为金属质地,传入中国后也出现了陶瓷、漆木和玻璃质地的仿制胡瓶。18世纪中期,当俄国斯特罗加诺夫(Stroganovs)家族成员在其彼尔姆(Perm)庄园里发现一件饰有阿娜希塔女神(Anahita)的萨珊银壶后(图三)[6],亚历山大·斯特罗加诺夫(A.Stroganov,1733-1811年)很快将它运送至法国巴黎做进一步的研究,并于1755年将成果在巴黎公开出版[7],从而开启了近代学界对萨珊胡瓶的研究历程[8]。
1970年,美利加·钦尔瓦尼(A.S.Melikian-Chirvani)首次将出土于粟特等地区、器型和花纹区别于萨珊金银器的部分器物称为“东伊朗组”金银器,并讨论了包括带把杯在内的粟特银器对唐代工艺的影响[9]。1971年,B.I.马尔沙克(B.I. Marshak)将粟特系胡瓶从原本统称为萨珊系胡瓶的分组中剥离出来[10]。目前学界通常认为胡瓶自中亚、西亚传入中土,主要分为粟特型、萨珊型及突厥型[11]。近年,随着美国芝加哥普利兹克艺术合作基金会(Pritzker Art Collaboratire)、卡塔尔阿勒萨尼基金会(The AI Thani Collection Foundation)、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The Cleveland Museum of Art)等海外机构、组织或个人收藏的胡瓶资料的公布[12],以及青海都兰热水墓群出土了数件金银胡瓶[13],为认识胡瓶的形制与工艺提供了重要材料。
国内胡瓶的考古实物基本明确为粟特型胡瓶的有两件。一是1975年内蒙古敖汉旗李家营子唐代墓葬出土一件鎏金胡人头像银执壶(图四),高28厘米,捶揲而成。齐东方认为此胡瓶具有典型的粟特风格,应为粟特产品[14],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托马斯·普利兹克(D.T. Pritzker)也认为此胡瓶很可能源自7-8世纪的粟特或中亚[15]。二是1984年河北宽城墓葬发现的一件素面银壶,口径6、通高36.5厘米。口与腹之间原有一柄,现已残缺(图五)[16]。
萨珊型胡瓶最具代表性的是1983年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墓出土的一件鎏金银瓶(图六),通高37厘米,具有典型的萨珊风格,据考证,此银壶的产地可能为中亚的巴克特里亚地区(Bactria)[17]。这三件国内出土的银壶为更好区分粟特型与萨珊型风格的胡瓶提供了最直观的素材。其中李贤墓鎏金银瓶与李家营子银执壶把手上方均有一人头像(图七),雕刻十分精细,其他胡瓶此处通常制作成一实心银质圆球,主要是在倾倒器内液体时能够更好地稳定器体。据观察,两处人头像均非中原人形象。李贤墓鎏金银瓶人头像,双眼大且外凸,高鼻梁,鼻翼较厚。双唇丰厚。头戴圆形花牙帽,头发卷曲。艺术史家H.克莱兹代尔(H.Clydesdale)认为此形象看起来像希腊人[18],而笔者认为更可能与中亚巴克特里亚人有关。李家营子银执壶人头像,深目高鼻,有八字胡须,短发后梳,为典型的中亚胡人形象。关于短发胡人,西安北周安伽墓石刻图案中共刻划人物115名,其中有88位剪发男性形象,民族属性均为粟特[19]。在史君墓石刻题材中出现人物123人,其中90人为男性,而男性中短发者亦有55例[20]。《魏书》记载中亚康国等有“丈夫剪发”[21]的风俗。《晋书》《北史》《旧唐书》中也可见类似记载。可见短发应是粟特民族男性流行的基本发式。
图五 河北宽城出土银壶
(采自河北博物院编《金银曜烁 美熠四方:京冀晋豫陕五省市金银器展》,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20年,第166页)
慕容智墓出土的素面银胡瓶(图八)与李家营子鎏金银执壶及河北宽城素面银壶在外观、器型上都有一定相似性,器型特点符合粟特胡瓶的主要特征:圈足较低,器颈较短、腹部圆鼓、把手下端与鼓起的腹部相接,上端直接与口沿相连。这在造型上与萨珊型胡瓶有着本质区别。
此外,俄罗斯彼尔姆地区(Perm District)出土的两件胡瓶与慕容智墓胡瓶在形制上也有诸多相似之处。
A.有翼骆驼纹鎏金银壶(图九),制作年代大约为700年,高39.7厘米,底座上有指示银壶重量的花剌子模(Khwarezmian)铭文,器身正面和背面的腹部各有两个大的团窠纹,里面都饰有一只带双翼的骆驼。壶体的其余表面、颈部和底座均饰有花卉和叶状图案。该器皿的弯曲手柄通过从龙头嘴中伸出的叶状结构连接到颈部,龙头标志着银壶把手最上面的曲线。该银壶原由斯特罗加诺夫(S.G.Stroganov,1794-1882)收藏,1925年转由俄罗斯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Hermitage)博物馆收藏[22]。银壶上装饰的有翼骆驼,正是粟特人喜爱的胜利之神韦雷斯拉格纳(Verethraghna或Warahrān),其职能包括充当旅行者的守护神等[23]。在片治肯特(Panjikent)一所房屋遗址的主墙上,绘有一男一女坐在带有动物形状支撑的长凳上,男子支撑物是骆驼,女子一侧的支撑物是公羊。另外两人手中各拿一盘,上面立一化身,男子的是双峰驼,女子的是公羊。这最有可能表达的是骆驼神瓦萨格恩(Wasagn)和其配偶瓦南克(Wannanc),而壁画上的两人可能是占据那所房子的粟特商人[24]。
B.素面金胡瓶(图一〇),其时代为7世纪末,高30.5、最大腹径18厘米,捶揲而成,颈部较短,腹部圆鼓,矮圈足直接与器身相连,圈足底沿饰一圈联珠纹,手柄与口沿连接处装饰一条有翼有角的龙的前部。目前收藏于俄罗斯国家历史博物馆。据马尔沙克考证,以上两件均为粟特系胡瓶[25]。而慕容智墓素面胡瓶造型上与这两件十分相似,进一步说明该素面胡瓶与中亚粟特胡瓶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一般认为,素面胡瓶的制作及流行年代可能较晚,但随着伊朗发现有5世纪素面金胡瓶(图一一),表明素面胡瓶已较早出现在波斯地区[26],胡瓶传入中亚地区后,其装饰图案及形制发生了变化。再向东传时,原先装饰图案的意境(如西亚的阿娜希塔女神及中亚的有翼驼)已无法融入当地文化,加之胡瓶的实用功能逐渐占据主要地位,繁缛精致的艺术装饰似乎已不再被工匠刻意表现。在萨珊时代早中期,工匠在制作每件作品时都使用了较多的装饰技术,包括雕刻、錾刻、镂刻、模锻压花、铸造、捶揲和鎏金等。而到了萨珊时代末期,对所有金属器使用较少的装饰技术再次受到时人青睐[27],这自然会影响到图案纹饰的加入。似乎在金银器装饰纹样输出的发源地——伊朗地区,素面已成为主流的审美趣味。可见胡瓶素面与否,与中古时期胡瓶自身发展历程有关,另外也与突厥民族的崛起及传入地民族的审美和选择有关。
第二突厥汗国毗伽可汗(公元713-734年)陵墓中出土了1850余件金银器,其中有数套金银酒具明器,酒具中包括金胡瓶、大浅盘、带鋬折肩罐和带把杯(图一二)[28],这些器具均为素面。其中素面带鋬折肩罐为突厥风格器皿,但混合了草原传统器型、突厥风格的折肩及粟特风格的鋬指等多种元素,此类器物在突厥墓中已发现多例,后来的唐五代契丹墓和辽墓中也屡见不鲜[29]。与突厥有密切来往的吐谷浑、吐蕃墓中也可见素面带鋬折肩罐[30]。
二、素面胡瓶的制作工艺及功用
(一)素面胡瓶的制作工艺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人员采用X射线衍射无损探伤、便携式XRF、SEM-EDS、金相显微等科学检测手段对慕容智墓银瓶进行了检测,其中运用X射线荧光能谱仪测出了银瓶不同部位的金属含量[31](表1)。总体来看,银壶并非纯银制品,材质为银铜合金,银瓶基体处银含量高达85.1%、铜含量达13.9%。
仔细观察,该胡瓶基体具有明显的捶揲痕迹,金相样品浸蚀后晶粒呈扁平条状分布的表象也予以证实银瓶确是采用了捶揲工艺。在制作该胡瓶时,工匠首先在一整块银铜合金的中心开始工作,捶揲形成圆形壶底,接着将金属片的两边重合焊接,因此可以发现银壶口沿处下方到壶身四分之一处有一长达20厘米的焊缝。后经打磨抛光,虽有焊痕但表面已较为平整。当胡瓶的圆鼓腹制作完毕后,工匠不断缩小金属片的宽度,内收形成粗短颈,然后制作出鸭嘴型的壶嘴。在此过程中还伴随有退火处理,以减轻金属在不断捶揲塑形中受到的张力。最后再巧妙地将壶身、圈足和手柄三部分焊接组成一完整的银壶。
出土时焊接处可见绿锈,经检测其焊料主要为银、铜和少量的锌[32]。具体到圈足与壶身、壶柄与壶身的焊料又有所不同,这与银壶的制作工艺及焊接顺序有关。圈足与壶身之间焊接使用的是银铜(Ag-Cu)焊药,银、铜是易形成低熔点共晶的合金,含铜的焊料置于焊点中,能降低焊点部位的熔解温度,增加流动性,利于快速焊接,且不易脱落,世界各地也都在使用。意大利金匠切利尼(B. Cellini)就曾将铜粉和银按1:2比例制成焊药,并命名为“Terzo”[33]。明代方以智《物理小识》中介绍其金银焊药的成分主要为铜,但“加银一分其中,永不脱”[34]。壶柄与壶身之间焊接使用的是银铜锌(Ag-Cu-Zn)焊药,当银中加入铜、锌元素时可形成三元共晶合金,它可使银焊药的熔点进一步降低,具有良好的湿润性和填充间隙的能力[35],因此常作为焊接溜缝的首选焊药。至此可以推断,当时工匠在制作完银壶基体后,先将圈足与壶体铆合焊接,然后再用熔点更低的银铜锌焊药将壶柄接上,体现出工匠的精心制作及对焊药特点的精准把握。
银壶中使用的铆合及焊接工艺在产自中亚巴克特里亚的鎏金银瓶和宽城素面胡瓶中都有所体现[36]。宽城素面银壶的X射线荧光分析结果显示其圈足与壶身应由同一块银板制成,后经焊接形成一带圈足的胡瓶,最后再焊接上手柄(图一三)。固原鎏金银瓶的制作工艺更为复杂,经X射线荧光检测来看,其壶口、把手左侧的壶身上腹和中腹,以及联珠上的圈足下边口所用材料都不相同,差异较大[37],工匠在制作该瓶时频繁使用了焊接工艺。总之,这类制作工艺有别于中国传统金属器常用的铸造法[38]。慕容智墓中的胡瓶可能为粟特商人从域外带来,或为粟特工匠在中国境内生产,抑或为中国工匠学习了中亚金属器的制造技艺后在本土制造。
(二)素面胡瓶的功用推测
慕容智墓中的胡瓶发现于棺内北侧墓主人头部附近,此外,同出的还有银罐、银盘及盘内装有金碟1件、凤鸟纹银蝶1件、银蝶3件、银折腹碗2件、银勺1件、银匙1件和银筷1双,共同组成一套完整的金银餐具。值得注意的是,胡瓶中盛有204克白葡萄酒液体、银罐内装有固体食物遗存。
目前中国所见的胡瓶形象主要分布于墓葬壁画、棺板画、石棺床绘画、石椁线刻画、陶瓷器以及敦煌壁画、绢画、纸画和考古出土实物中。
以北朝至隋的入华粟特裔使用的石椁或石棺床上出现的胡瓶及其场景为例。隋代虞弘墓(592年)中共有5处出现了胡瓶形象,椁壁浮雕第5幅、椁座前壁浮雕下栏第2幅、椁座后壁浮雕上栏第4幅和第5幅以及一男侍从俑手抱胡瓶[39]。椁壁浮雕中的胡瓶都出现于宴饮场合,尤其椁壁浮雕第5幅画面中的右下方有一较大的胡瓶,另侍从手中也抱一胡瓶,画面中央的男女主人公一人手拿多曲长杯、一人手握高足小酒杯。
北周安伽墓(579年)中围屏石榻上的正面屏风第3幅和第5幅、左侧屏风第3幅帐外及右侧屏风第2幅帐前右侧等多处出现胡瓶形象[40],这几幅屏风展现的都是与宴饮有关的场面,高足酒杯、来通等酒具并伴随出现。北周史君墓(580年)中出土石椁上的南壁第1幅和第5幅、西壁第2幅及北壁第4幅浮雕[41]出现了胡瓶形象。尤其石堂北壁第4幅浮雕描绘的是男女主人在葡萄园中与宾客尽情宴饮的欢快场面(图一四),所用酒具除了胡瓶以外,还有长杯、来通、高足酒杯和喇叭形酒杯等。胡瓶和酒杯中大概率盛放的就是胡人喜爱饮用的葡萄酒。
此外,甘肃天水市发现的石马坪屏风石棺床、日本Miho美术馆收藏的北齐石棺床、法国吉美博物馆收藏的围屏石榻及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藏北齐画像石屏中都出现了胡瓶等酒具及在葡萄园宴饮场景。而这些石棺或石榻据考证都与粟特有关或直接为粟特裔所使用[42]。这表明胡瓶大多是在粟特人的宴饮场合中使用。
从唐代的诗歌、壁画、墓中随葬的陶俑、石刻、玉器、金银器等不同层面均可看到胡人的痕迹,在多处唐墓壁画中都可见到胡瓶的形象。如房陵长公主墓(673年)前室东壁南侧《托盘执壶侍女图》和后室北壁《提壶持杯侍女图》壁画中的女侍从穿着胡服,一手持多曲长杯、一手持胡瓶,还有一女侍从一手持高足杯、一手持胡瓶。与慕容智墓出土胡瓶形象较为接近的是李震墓(660年)第三过洞东壁侍女左手中的执壶,及李凤墓甬道东壁一仕女左手中的执壶[43],它们仅在圈足、颈部长短等局部与慕容智墓素面胡瓶有细微差别。
与李家营子素面胡瓶同出的还有小银壶、椭圆银杯、猞猁纹鎏金银盘和银勺[44]。这几件银器恰好组成一套餐饮用具,简洁、实用,又便于携带,可能为粟特胡商所使用。宽城发现的素面银壶也与一件三足鹿纹鎏金银盘同出。这两件银壶据研究应为粟特银器输入品[45],值得注意的是,慕容智墓中与银胡瓶同出的还有银罐、银盘、银碗等成套餐饮器具,这与敖汉旗李家营子的情况十分相似。另在慕容智棺外西北角,有一漆盘,里面放置了7件漆碗、1件银匙、1副银筷,组成一套用具。7件漆碗均为侈口、弧腹内收,腰部饰一圈横折棱,平底,有矮圈足[46]。与棺内银盘中的银折腹碗形制如出一辙,除了盛放干果外,此类折腹碗也可作为饮用葡萄酒的酒器。
吐谷浑、吐蕃王室时常向粟特人订制包括胡瓶在内的器具,如美国芝加哥普利兹克收藏的神鸟神兽纹嵌绿松石金胡瓶及阿勒萨尼收藏的嵌绿松石饰兽鸟纹胡瓶、金瓶和金盘。这些器具是粟特工匠为吐蕃王室特意制作的,迎合其审美和品味,代表了粟特工艺的高超水准[47]。吐蕃王室与唐王朝交往过程中,经常将包括胡瓶在内的成套酒具作为国礼呈上。这些器具可能就是吐蕃从粟特那里订制而来,尤为珍贵。《旧唐书·吐蕃传》载,开元十七年(729年)吐蕃赞普向唐朝递交请和文书,并“谨奉金胡瓶一、金盘一、金椀一、马脑杯一、零羊衫段一,谨充微国之礼。金城公主又别进金鹅、盘盏杂器物等”[48]。开元二十年(733年),吐蕃又“今奉皇帝金铨、马脑、胡瓶、羚羊衫段、金银瓶盘器等,以充国信”[49]。贞观二十年(646年)唐太宗伐辽东还,吐蕃遣使节禄东赞来贺,奉表称“夫鹅,犹雁也,故作金鹅献。其鹅黄金铸成,其高七尺,中可实酒三斛。”[50]吐蕃常特制金鹅状酒器送给唐朝皇室,以加深与唐朝的甥舅情谊。据青海出土吐蕃时期彩绘棺板画上的胡瓶图像来看(图一五)[51],吐蕃进贡的胡瓶也应为酒器,并常与金盘、金碗、高足杯、金银盏器等配套使用。
隋唐时期,史料中不乏有朝廷皇室赏赐功臣胡瓶的记载。譬如唐太宗时期,凉州总督李大亮因劝谏有功,而被皇帝赏赐一御用胡瓶。史照《通鉴释文》以为汲水器,胡三省在《通鉴释文辩误》卷九中写道:“唐太宗赐李大亮胡缾。盖酒器也,非汲水器也。今北人酌酒以相劝酬者,以曰胡缾,未识其规制与太宗之胡瓶合乎否也。缾、瓶字通。”[52]说明宋元时期人们依然认为唐代胡瓶是酒器而非汲水器。
最后将视角转移至胡瓶底部的刻字上(图一六)。结合目前发现的窖藏和墓葬出土金银器来看,初唐时的金银器较少出现刻铭,中晚唐金银器上的刻铭明显增多,内容多为人名、地名、时间或器物重量等。原报告记瓶底刻划有一“观”字,但仔细观察,瓶底可能仍有其他字存在,疑似为“贞”“十”等。结合胡瓶等配套器具的使用和磨损痕迹,推测其为慕容智生前享用家宴时经常使用的一套实用酒具,在墓主死后一并葬入墓中,且安置在棺内北侧墓主人头部附近,以示其珍贵和深受墓主人的喜爱。
三、中国现存最早的白葡萄酒及葡萄酒的东传
当考古人员发现该胡瓶时,瓶口仍有黄布包裹的封泥和木塞残渣,后经中国科学院大学实验室称重和检测,认为胡瓶里204克左右的绿色液体具有白葡萄酒的主要成分及特征[53]。慕容智墓中发现的白葡萄酒遗存,是迄今为止国内白葡萄酒实物的首次发现。
中国科学院大学专业人员检测后,判断胡瓶里的液体为白葡萄酒。首先是因为在液体中发现白葡萄酒特有的山奈酚衍生物。其次检测结果显示液体中酒石酸(Tartaric acid)含量较高、同时含有葡萄酒的其他特有标记物。酒石酸是葡萄中存在的天然物质,一般占到葡萄酒总量的1/4~1/3,高酒石酸特征表明其为葡萄酒遗存。早在20世纪90年代,生物考古学家麦戈文(P. McGovern)指出一些有机酸可作为酒类遗存的标记物[54],如酒石酸指示葡萄酒,草酸指示啤酒。此后学界进行了大量以酒石酸、草酸等有机酸作为酒类标记物的研究,比如瓜什-简妮(M. R. Guasch-Jane)等人以酒石酸、丁香酸作为红葡萄酒的标记物发现古埃及图坦卡蒙墓有将红、白葡萄酒分开摆放的奇特葬俗[55]。丁香酸是一种锦葵色素的降解产物,锦葵色素-葡糖苷是让新鲜红葡萄酒呈现红色的主要成份。随着酒的年代增加,锦葵色素与其它成分发生反应形成更复杂的结构,这些复杂结构打破之后会释放出丁香酸[56]。而慕容智墓银瓶液体中呈现无丁香酸(Syringic acid)特征,可间接推断银瓶中204克液体为白葡萄酒,这可能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白葡萄酒。
现代仪器检测显示,红、白葡萄酒在其成分及酚类物质方面存在明显区别[57]。所谓白葡萄酒,即是几乎不含红色素(花色素苷)的葡萄酒,它包括用白色品种酿成的白葡萄酒和用红色品种去皮后酿成的白葡萄酒两大类[58]。此外,胡瓶里的液体还包含酿酒酵母、曲霉、乳酸菌以及大麦、小麦等粮食作物的特异性肽段,表明该白葡萄酒中可能使用了酒曲发酵[59],并采用葡萄与粮食混酿的工艺。《唐会要》载:“及破高昌,收马乳葡萄实,于苑中种之,并得其酒法,帝自损益造酒。酒成,凡有八色,芳香酷烈,味兼醍醐,既颁赐群臣,京中始识其味。”[60]可见,唐太宗破高昌得到马乳葡萄良种后,亲自对葡萄酒酿造工艺进行试验,或许就是对高昌葡萄自然发酵酿酒法进行改造,并运用添加酒曲等中国传统酿酒技术,最终成功制出多种颜色、风味的葡萄酒。此外,宋人朱肱及金人元好问对用粮食和葡萄加曲混酿的古法也有所记载[61]。
迹象表明,胡瓶里时常盛放的是粟特人爱喝的葡萄酒[62]。从中亚片治肯特城壁画中我们可以看到,宴客享用的水果种类繁多,其中最常见的就是葡萄(图一七),这是葡萄物种在中亚盛产的实际体现。粟特人在宴会上沉迷于葡萄酒,从兽角来通中流出的液体通常是红色的,葡萄酒在中亚的流行有其独特的文化背景。而在穆格山城堡发现的8世纪粟特文献中,在粟特历2月28日举行的晚宴中,葡萄酒也是被提及的唯一饮品。一份由葡萄酒商人撰写的文书列出了在特定日期交付了若干卡皮查(Kapicha,粟特度量)葡萄酒[63]。另一封来自片治肯特统治者戴瓦什提契(Devashtichy)的信中说,在他的信到达收件人后,应该将芳香的葡萄酒送给突厥军事指挥官[64]。与萨珊波斯一样,饮酒是粟特宴会的核心。这几份文书显示,即使在8世纪上半叶,粟特人仍然可以靠经销葡萄酒获取利润,且酿造的葡萄酒常受到粟特和突厥上层人物的喜爱。
图一七 塔吉克斯坦片治肯特古城壁画贵族宴饮果盘里有葡萄
(采自Betty Hensellek, A Sogdian Drinking Game at Panjikent, Iranian Studies, 2019(52): 838.)
随着中原葡萄种植业的发展和西域胡人的入华,西域葡萄酒开始进入中原人的生活。1975年,在天山北麓的一座古墓中发掘出酿酒器具一套,距今约2000年,其中有球形青铜壶、扁形陶瓷发酵器和木制压榨葡萄的工具[65]。说明至少在两汉之际新疆地区已开始酿造葡萄酒。西域酿造出的葡萄酒直至南北朝时在汉地仍很珍贵稀少,高昌王麴坚遣使朝贡南朝梁时,就把葡萄和葡萄酒当做上等方物献给梁武帝萧衍(464-549年)。
在葡萄及葡萄酒东传过程中,凉州是重要的一站。从《后汉书》中扶风孟佗“以葡萄酒一升遗张让,即拜凉州刺史”[66]的记载即可从侧面看出东汉时葡萄酒的名贵。武周时期,凉州是全国重要的经济中心之一。3世纪末至4世纪初,粟特人东迁活动已展开[67],除了较为熟悉的西州崇化乡和敦煌从化乡居住着大量粟特人之外[68],还有众多入华粟特人在凉州聚居,《安令节墓志铭》等材料[69]表明,西域胡人家族入华过程中常将武威作为落脚点或中转站。《北史·西域传》也记载粟特商人多诣凉土贩货[70]。
众多粟特人在凉州生活、聚居,为葡萄酒酿造技术传入凉州并在凉州继续发展创造了机会。慕容智墓葬里出土装有白葡萄酒的胡瓶并不让人感到十分意外。凉州及其周边是葡萄酒自西域东传的第一站,且早在东汉时期凉州葡萄酒已负盛名,到了隋唐时期已闻名遐迩,法国学者童丕(E.Trombert)认为,到了盛唐时期,来自吐鲁番、凉州等地的葡萄酒已基本可以满足汉地的需要,中原人已从粟特人那学会了葡萄酒酿造技术[71]。
四、结语
一次考古发掘往往会产生一组似乎与某一特定人群活动有关的数据,尤其当某种对特定的植物或动物具有高度特异性的有机化合物被保存下来并得以识别,这一证据很可能成为考古学家阐释考古现象时的重要锁钥。慕容智墓出土胡瓶中的白葡萄酒正是如此,为探讨唐代胡瓶本身及其白葡萄酒酿造工艺发展、葡萄酒东传、粟特人在武威及丝路沿线的相关活动等问题提供了重要机遇。综上所述,可初步得到以下两点认识。
第一,慕容智墓出土的素面胡瓶在器型上与国内河北宽城出土银壶及内蒙古敖汉旗李家营子出土银执壶较为相似,同类型器物还有俄罗斯彼尔姆地区出土的两件胡瓶。此外,慕容智墓胡瓶制作采用了捶揲、铆合、焊接等工艺,与中亚金银器制作工艺存在渊源关系。表明该胡瓶与粟特型胡瓶有一定的关联性,可能为粟特商人从域外带来,或为粟特工匠在中国境内生产,抑或为中国工匠学习了中亚金属器的制造技艺后在本土制造,制作年代大致在7世纪中期或更早。与胡瓶同出的还有银罐、银盘以及盘内的碗、蝶、筷、勺、匙,共同组成一套完整的金银餐具。且这些器具均为素面,胡瓶素面与否与中古时期胡瓶自身发展历程有关,另外也与突厥民族的崛起及传入地民族的审美和选择有关。
第二,胡瓶中盛有204克的白葡萄酒,这是目前中国现存最早的白葡萄酒实物,成为考古上首次发现胡瓶功用主要为酒器的力证。白葡萄酒中还包含酿酒酵母、曲霉、乳酸菌以及大麦、小麦等粮食作物的特异性肽段,表明该白葡萄酒的酿造工艺采用的应为史料记载中的用粮食和葡萄加曲混酿法。慕容智墓胡瓶中的白葡萄酒体现出唐朝葡萄酒酿造工艺的创新和发展。
该墓是目前发现唯一保存完整的吐谷浑王族墓葬,所出器物对于探讨古代丝绸之路沿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凉州(武威)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历史地位及异域文化对于河西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影响等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1]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甘肃武威市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考古》2022年第10期。
[2] 刘兵兵等《唐〈慕容智墓志〉考释》,《考古与文物》2021年第2期;李宗俊《吐谷浑喜王慕容智墓志及相关问题》,《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
[3] 刘兵兵等《唐〈慕容智墓志〉考释》,《考古与文物》2021年第2期。
[4] 同[3];沙武田、陈国科《武威吐谷浑王族墓选址与葬俗探析》,《考古与文物》2021年第2期;李宗俊《吐谷浑喜王慕容智墓志及相关问题》,《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杨瑾《甘肃武威慕容智墓披袍俑的多元文化渊源探析》,《中原文物》2022年第4期;陈国科《武威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考古发现与研究综述》,《王国的背影——吐谷浑慕容智墓出土文物》,文物出版社,2022年;顾文婷等《武威慕容智墓壁画颜料分析及制作工艺研究》,《文博》2023年第3期。
[5]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王国的背影——吐谷浑慕容智墓出土文物》,第138页,文物出版社,2022年。
[6] B.I. Marshak, Late-Antique Silver, Penelope Hunter-Stiebel, Stroganoff: The Palace and Collections of a Russian Noble Family, Harry N. Abrams, 2000,p.101.
[7] 原载Comptes rendus de l'Acade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 1755(30).此据B.I.Marshak,Late-Antique Silver, Penelope Hunter-Stiebel, Stroganoff: The Palace and Collections of a Russian Noble Family, Harry N. Abrams,2000, pp.101-102.
[8] 参见J.Orbel, Sasanian and Early Islamic Metalwork, A.U.Pope, A Survey of Persian Art from prehistoric Times to the Present, Vol.Ⅱ, Meiji-Shobo, 1981, pp.716-770;Oleg Grabar, Sasanian Silver: Late Antique and Early Medieval Arts of Luxury from Ir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Museum of Art, 1967, pp.61-66;深井晋司《アナ—ヒタ—女神裝飾鍍金銀製把手付水瓶——所謂‘胡瓶’の源流問題について》,氏著《ぺルシア古美術研究·がラス器·金属器》,第145-166页,吉川弘文館,1968年;Б.И.Маршак, Согдийское серебро, Москва, 1971;M.L.Carter, Royal Festal Themes in Sasanian Silverwork and their Central Asian Parallels, Acta Iranica I, 1974,pp.171-202;田辺勝美:《シルクロードの贵金屬工兿》,第29-59页,有限會社シマレ,1981年;B.I.Marshak, Silberschätze des Orients: Metallkunst des 3.-13. Jahrhunderts und ihre Kontinuität, E.A.Seemann,1986等。
[9] A.S.Melikian-Chirvani,Iranian Silver and Its Influence in T'ang China, William Watson ed.,Pottery and Metalwork in T'ang China,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1970, pp.12-18.
[10] 参见Б.И.Маршак,Согдийское серебро, Москва, 1971, pp.41-46;[俄]鲍里斯·艾里克·马尔沙克著,李梅田等译《粟特银器》,第42-5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
[11] 关于胡瓶的种类观点并不一致,如齐东方认为主要有萨珊系统和粟特系统,但其他金银器中除此之外,还有拜占庭-东罗马和印度、贵霜、嚈哒、突厥、阿拉伯等文化因素(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第305-32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李雨生等提出陕西庆山寺上方舍利塔基出土铜壶还具有印度文化因素(李雨生等《陕西临潼唐庆山寺上方舍利塔基出土铜壶研究》,《考古》2018年第11期);还有学者认为有波斯、粟特、突厥三种类型[朱建军《青海都兰古墓葬遗址新获文物调查与研究》,《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12] 参见王旭东、[美]汤姆·普利兹克主编《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吐蕃时期艺术珍品》,第118、210-214页,中国藏学出版社,2020年;霍巍《一批流散海外的吐蕃文物的初步考察》,《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年第5期;Amy Heller, Tibetan Inscriptions on Ancient Silver and Gold Vessels and Artefacts,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Bon Research, 2013(1):259-291;Frantz Grenet, The Deydier Vase and Its Tibetan Connections: A Preliminary Note, Interaction in the Himalayas and Central Asia, 2017, pp.91-103;霍巍、祝铭《20世纪以来吐蕃金银器的发现与研究》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1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青海都兰县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考古》2021年第8期。
[14] 敖汗旗文化馆《敖汗旗李家营子出土的金银器》,《考古》1978年第2期;齐东方《李家营子出土的粟特银器与草原丝绸之路》,《北京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
[15] David Thomas Pritzker, Allegories of Kingship: A Preliminary Study of a Western Central Asian Gold Ewer in the Royal Court of Tibet, Eva Allinger et al.,Interaction in the Himalayas and Central Asia: Processes of Transfer, Transl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Art, Archaeology, Religion and Polity, Austrian Academy of Sciences Press, 2017, p.107.
[16] 宽城县文物保护管理所《河北宽城出土两件唐代银器》,《考古》1985年第9期。
[17] 罗丰《北周李贤墓出土的中亚风格鎏金银瓶——以巴克特里亚金属制品为中心》,《考古学报》2000年第3期,收入《胡汉之间——“丝绸之路”与西北历史考古》(修订本),文物出版社,2022年。
[18] Heather Clydesdale, Objects of Fascination: Encountering Six Dynasties China through Material Culture, Education About Asia, 2021(36):34.
[19]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著《西安北周安伽墓》,第73页,文物出版社,2003年。
[20] 西安市文物保护研究院编著《北周史君墓》,第190页,文物出版社,2014年。
[21]《魏书》卷一二〇《西域传》,第2281页,中华书局,1974年。
[22]В.П.Даркевич,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й металл Востока VIII-XIII вв.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восточной торевтики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европейской части СССР и Зауралья,Наука, 1976, pp.23-24,85;奈良県立美術館編集《シルクロード・オアシスと草原の道》,第167页,奈良県立美術館,1988年。
[23] 孙机《建国以来西方古器物在我国的发现与研究》,《文物》1999年第10期;Judith A.Lerner,Sogdian metalworking, The Sogdians: Influencers on the Silk Roads, Freer and Sackler Galleries online exhibition, 2019.
[24] B.I.Marshak, Legends, Tales, and Fables in the Art of Sogdiana, Bibliotheca Persica Press, 2002, p.16.
[25] [俄]鲍里斯·艾里克·马尔沙克著,李梅田等译《粟特银器》,第3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
[26] 東京國立博物館等編《シルクロードの遺宝―古代・中世の東西文化交流》,第149図,日本經濟新聞社,1985年。
[27] Ann C.Gunter and Paul Jett, Ancient Iranian metalwork in the Arthur M.Sackler Gallery and the Freer Gallery of Art,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1992, pp.52-53.
[28] Turkish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 ed., Work for the Project Turkish Monuments in Mongolia in Year 2001, Ankara,2003; Hasan Bahar, The Excavation and the Conservation of Bilge Khan Monumental Grave Complex in Mongolia, 22nd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Document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CIPA) Symposium, October 11-15, 2009, Kyoto, Japan Proceedings, 2009.
[29] 孙机《论近年内蒙古出土的突厥与突厥式金银器》,《文物》1993年第8期;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第321-33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林梅村《松漠之间:考古新发现所见中外文化交流》,第224-237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陈凌《突厥汗国与欧亚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第31-34、109-11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30] 仝涛《甘肃肃南大长岭吐蕃墓葬的考古学观察》,《考古》2018年第6期。
[31] 张伟等《甘肃武威慕容智墓出土银壶制作工艺研究》,《石窟与土遗址保护研究》2022年第4期。
[32] 同[31]。
[33] Benvenuto Cellini, Translated By C. R. Ashbee, The Treatises of Benvenuto Cellini on goldsmithing and Sculpture, Dover Publications, 1967, pp.10-11.
[34] (明)方以智著,陈文涛笺证《方以智物理小识》,第96页,文明书局,1937年。
[35] 杨小林《中国细金工艺与文物》,第126页,科学出版社 , 2008年。
[36] 李虎候等《几种古代银器的X射线荧光分析》,《考古》1988年第1期;罗丰《胡汉之间——“丝绸之路”与西北历史考古》(修订本),第155-157页,文物出版社,2022年。
[37] 李虎候等《几种古代银器的X射线荧光分析》,《考古》1988年第1期。
[38] [日]中野徹《唐代金银器形式的变迁和制作方法》,《中国艺术文物讨论会论文集》下册,第599-600页,台北故宫博物院,1993年。
[39]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编著《太原隋虞弘墓》,第20、21、135、147、148页,文物出版社,2005年。
[40] 同[19],第24、30、33、37页。
[41] 同[20],第88、98、105、131页。
[42] 天水市博物馆《天水市发现隋唐屏风石棺床墓》,《考古》1992年第1期;姜伯勤《图像证史:入华粟特人祆教艺术与中华礼制艺术的互动——Miho博物馆所藏北朝画像石研究》,《艺术史研究》第3辑,第241-249页,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東京国立博物館編《シルクロード大美術展》,第39页,読売新聞社,1996年;J.J.Lally & Co., Chinese Archaic Bronzes, Sculpture and Works of Art, New York, 1992, pl.6-7.
[43] 张鸿修编著《中国唐墓壁画集》,第41、72页,岭南美术出版社,1995年。
[44] 敖汉旗文化馆《敖汉旗李家营子出土的金银器》,《考古》1978年第2期。
[45] 齐东方等《唐代金银器皿与西方文化的关系》,《考古学报》1994年第2期。
[46] 同[5],第181-183页。
[47] 王旭东、[美]汤姆·普利兹克主编《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吐蕃时期艺术珍品》,第162、163、210-215页。
[48]《旧唐书》卷一九六《吐蕃传》,第5231页,中华书局,1975年。
[49](宋)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九七九《外臣部二十四·和亲二》,第11335页,凤凰出版社,2006年。
[50] 同[48],第5222页。
[51] 青海省博物馆编著《尘封千年的岁月记忆:丝绸之路(青海道)沿线古代彩绘木棺板画》,第150-152页,文物出版社,2019年;Amy Heller, Observations on Painted Coffin Panels of the Tibetan Empire, Christoph Cuppers, Robert mayer, Michael Waltereds.,Tibet after Empire: Culture, Society and Religion between 850-1000 Proceedings of the Seminar Held in Lumbini, Nepal, March 2011, Dongol Printers,2013,pp.117-168.
[52](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附录《通鉴释文辩误》卷九,第125页,中华书局,1956年。
[53] 笔者之一罗丰在与中国社科院大学杨益民教授个人通讯中得知:其团队在对胡瓶所盛液体的前期分析中,发现多种发酵产物,包括乙酸、酒石酸、乳酸、琥珀酸等多种有机酸,甘油醛、乙偶姻、苯乙醇、苯甲醛、1,2-丙二醇、甘油、2,3-丁二醇、1,2,3-丁三醇等物质。其中,甘油、乙偶姻、2,3-丁二醇是典型的发酵副产品,为葡萄酒带来特殊风味、口感。通过“高酒石酸,无丁香酸”的特征判断葡萄酒为白葡萄酒。此外,还发现山奈酚(白葡萄酒特有)的衍生物。在后续的蛋白质组学研究中,进一步发现了酿酒酵母、曲霉、乳酸菌以及大麦、小麦、粳稻、籼稻、豌豆、黍亚科植物的特异性肽段。高琥珀酸、乳酸、草酸的特点,应当也与原料中存在粮食有关。综合以上结果,其团队推测该样品是葡萄酒技术与中国曲酒技术的融合产品。目前有两种解释,其一是唐宋文献中记载的一种中国本土化的葡萄酒,即以葡萄、蒸熟的粮食为原料,添加酒曲酿造(葡萄酒酿造过程本不需要酒曲)。其二是白葡萄酒、曲酒在酿造完成后调和而成。后一种情况似乎不合常理,但目前并不能严格排除。由于新的研究进展,结论有所更新,但不影响原有的“白葡萄酒”部分认识。
[54] P.E.McGovern, et al., Neolithic resined Wine, Nature, 1996(381): 480–481.
[55] Maria Rosa Guasch-Jane et al., Liquid Chromatography with Mass Spectrometry in Tandem Mode Applied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Wine Markers in Residues from Ancient Egyptian Vessels, Analytical Chemistry, 2004(76):1673.
[56] Vernon L. Singleton, An Enologist’s Commentary on Ancient Wines, The origins and ancient history of wine, Gordon & Breach Publishers: Philadelphia,Routledeg, 2005, pp.67-77;丁燕《最新研究发现:古埃及法老喜欢红葡萄酒》,《中外葡萄与葡萄酒》2004年第2期。
[57] 朱宝镛主编《葡萄酒工业手册》,第551页,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95年。
[58] 李华编著《葡萄酒品尝学》,第26页,科学出版社,2006年。
[59] 古代生产的葡萄酒一般分为两类:一是原酿葡萄酒,采取中国酿酒的传统习惯,使用酒曲发酵工艺,在葡萄浆中加入酒曲,催使其发酵成熟;二是葡萄蒸馏酒,葡萄蒸馏酒采取的是蒸馏工艺,提取酒精度更高的蒸馏葡萄酒。
[60](宋)王溥《唐会要》卷一〇〇《杂录》,第1796、1797页,中华书局,1960年。
[61] 详参朱肱《北山酒经》和元好问《葡萄酒赋并序》,(宋)朱肱等撰,任仁仁整理校点《北山酒经:外十种》,第37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年;(金)元好问《遗山集》卷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91册,第5、6页,(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
[62] 参见仲高《丝绸之路上的葡萄种植业》,《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陈习刚《唐代葡萄酒产地考——从吐鲁番文书入手》,《古今农业》2006年第3期;[法]童丕著,阿米娜译《中国北方的粟特遗存——山西的葡萄种植业》,《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中华书局,2005年;王光尧《古代葡萄酒酿造技术的东来及变化——海外考古调查札记(八)》,《故宫博物院院刊》2022年第6期。
[63]M.N.Bogolyubov,O.I.Smirnova, Sogdian Documents from Mount Mugh: Reading,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Issue IIl, Business documents, Eastern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63, pp.29-31.
[64] Nicholas Sims-Williams, Corpus Inscriptionum lranicarum, Part II:Inscriptions of the Seleucid and Parthian Periods and of Eastern Iran and Central Asia,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2015, pp.115-118.
[65] 卫斯《唐代以前我国西域种植葡萄历史疏证》,《西域研究》2005年专刊。
[66]《后汉书》卷七八《宦者列传》,第2534页,中华书局,1973年。
[67] [日]石见清裕《浅谈粟特人的东方迁徙》,《唐史论丛》2016年第2期。
[68] 参见 [日]池田温著,辛德勇译《八世纪中叶敦煌的粟特人聚落》,《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9卷《民族交通》,中华书局,1993年;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第154~197页,文物出版社,1994年。
[69]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册,第669、104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70] 《北史》卷九七《西域传》,第3221页,中华书局,1974年。
[71] [法]童丕著,阿米娜译《中国北方的粟特遗存——山西的葡萄种植业》,《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第205-225页,中华书局,2005年。
作者:罗丰、曹中俊(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丝绸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
本文原载《文物》2024年第7期
文章来源:丝绸之路 公众号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rAOuXI-R_1grMe0RrWcNR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