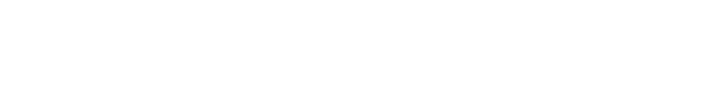杨岐黄 | 距今4300年前后玉文化发展的新态势——从新石器时代两次玉文化发展高峰入手
摘要:距今4300年前后是考古学文化发展的重要时间节点,也是古国向王国演进的关键阶段。这一时期在海岱、晋南、陕北、甘青、长江中游地区以山东龙山文化、陶寺文化、石峁文化、齐家文化、后石家河文化等为代表的多个用玉、制玉中心发展起来,形成了新石器时代玉文化发展的第二次高峰,展现出各玉文化同时并存、相互影响,各地区和各玉文化存在多个中心,玉文化发展存在南北模式等新的阶段特点。玉器作为文明进程的重要指针,这一阶段玉文化在发展重心、礼仪系统及角色转换等方面表现出的新态势,是文明进程中社会复杂化、文化整合统一等意识形态方面变化的反映。
距今4300年是中华文明进程中古国时代早晚两段的时间节点[1]。碳十四系列测年结果也显示,4300年是诸多考古学文化的起始时间。其后的500年,属于龙山时代,在这一阶段中国史前传统文化格局发生重大调整,新兴资源重新配置,社会结构进行了大规模整合重组,是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关键时段,也是古国向王国时代演进的关键阶段[2]。
在此关键阶段,玉文化的发展也呈现出新的格局与态势。在海岱、晋南、陕北、甘青、长江中游地区发展出以山东龙山文化、陶寺文化、石峁文化、齐家文化、后石家河文化(肖家屋脊文化)等为代表的多个用玉、制玉中心。(图一)除了海岱地区外,其他区域都是新发展起来的玉文化中心;各中心同时并存又相互影响,并且每个中心都存在多个代表性的遗址,可视为分中心或次中心;另外玉文化的发展也呈现出鲜明的南北模式[3]。
图一 距今4300年前后玉文化中心的分布情况
对于这一阶段玉器发展的基本脉络,已有学者作专文讨论[4]。但是纵观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玉器玉文化发展,存在两次大的发展高峰:第一次大致是在5300年前后,以凌家滩文化、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玉文化为代表;第二次大致是在4300年前后,以山东龙山文化、陶寺文化、石峁文化、齐家文化、后石家河文化玉文化为代表。值得关注的是,这两次玉文化高峰见证了中华文明进程中古国的形成与发展,孕育了王国的形成,两次玉文化发展高峰与文明进程中两个重要节点相关联。因此本文拟以距今4300年前后玉文化发展的新态势为切入点,通过对两次玉文化发展高峰的比较,观察这一阶段玉器玉文化发展与演变的新特点,并尝试探求玉器玉文化在文明进程和社会复杂化过程中的表现与作用。
第一次玉文化发展高峰中各玉文化时代相继,个性鲜明,具有承继关系;第二次玉文化发展高峰中的各玉文化时代相当,多中心一体,难分伯仲。
第一次玉文化发展高峰阶段,凌家滩文化(距今5600—5300年[5])、红山文化(距今5500—5000年[6])、良渚文化(距今5300—4300年)等代表性玉文化,发展时代相继,有承继和延续发展的特点。三个代表性文化集独特的玉器种类、造型纹样、制作工艺、用玉习俗、玉料等于一身,是完整又独立的制玉、用玉中心,个性鲜明,在文化传播中具有很强的辨识度。(图二)
图二 第一次玉文化发展高峰阶段三个代表性文化的部分典型器物与纹饰
与此同时,各文化间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凌家滩和红山文化中就有很多造型和使用上都非常相似的器物,如玉龙、玉猪、玉鸟、玉人等,两者间应有某种紧密联系,或者具有某种共同的信仰体系,也不排除有人群的直接交流。最后发展起来的良渚文化玉器,集两者玉文化发展之大成,尤其是承继了凌家滩玉文化传统,形成了相对成熟的玉器使用体系及与其对应的相对完善的宗教体系。三个文化皆流行趋坛而葬[7]、贵族墓与祭坛一体化,流行玉敛葬,而且红山文化中普遍以石构筑祭坛,凌家滩文化也以石块来构筑祭坛,良渚的瑶山和汇观山遗址是土石结合的,而其他太湖流域的祭坛遗址都是土筑,可见三个文化间确实有着微妙的联系[8]。
第二次玉文化发展高峰阶段,海岱地区受到燕辽地区、长江下游地区玉文化的影响,经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玉器体系逐步发展起来。其他玉文化中心区域,虽然在此之前都有一些零星的玉器发现,但是都没有形成规模,形成玉器制作与使用的中心。
玉文化中心的形成应该具有三个条件:一是稳定的玉料来源;二是成熟的制玉工艺;三是赋予玉器特殊功能的宗教信仰或礼仪体系。第一点是有就近分布的玉矿或者通过某种途径可以稳定地获得玉料。在这一阶段,随着跨区域互动网络的形成与互动[9],玉料作为珍稀资料在各文化圈顺畅流通,不再是局限玉文化中心形成的资源性条件,掌握玉料流通的遗址或文化,也可以成为玉文化中心,如石峁、陶寺、后石家河文化等。第二点是成熟的制玉工艺,由于玉本身的物理特性,玉作工艺比石作工艺对工具和技术的要求更高。第三点最为重要,如果在宗教信仰或者礼仪体系中并不尊崇玉器,或者玉制品并没有被赋予一些特殊的含义或者功能,那么即使在玉料产地也不容易形成用玉中心。
从各个玉文化流行的绝对年代看,海岱地区龙山文化(距今4300—3900年[10]),晋南地区陶寺文化(距今4300—3900年[11]),陕北地区石峁文化(距今4300—3800年[12]),甘青地区齐家文化(距今4200—3600年[13]),长江中游地区后石家河文化(肖家屋脊文化)(距今4200—3800年[14]),表现出非常强的集中性。各玉文化的发展时间基本相同,几乎同时出现,又同时消亡。齐家文化的延续时间较长一些,但是齐家文化晚期玉器衰落,仅余零星的绿松石饰品,玉文化的发展时间段仍与其他文化一致。陶寺和石峁文化是两个对玉器进行整合发展的玉文化,而且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甘青与海岱地区的枢纽。山东龙山文化的玉器发展承继了大汶口文化的传统,发展时间长,体系相对完备。再有齐家、后石家河文化(肖家屋脊文化)玉器,对当时周边玉文化,以及二里头玉文化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从玉文化发展的角度而言,这一时期各文化的发展旗鼓相当,难分伯仲。
北方地区玉文化呈现出趋同的趋势[15]。(图三)有些器物,如玉壁环,如果脱离出土背景,简单从器形、制作工艺等方面来推断其文化属性究竟是属于陶寺文化、石峁文化还是山东龙山文化十分不易。而且各玉文化中都能见到同时的数个玉文化中的典型器物。如石峁文化就出土有后石家河文化的玉虎头、鹰形笄等,齐家文化的宽体多片璜联璧,陶寺文化的璜联璧、瑗式璧,山东龙山文化牙璧等。这些各文化的代表性器物在短时间内出现在周边其他文化中,反映出各文化间有着顺畅和频繁的交流与影响。
图三 北方地区玉文化中部分同类器物器形比较
从以上方面看,第二次玉文化发展高峰阶段,各个玉文化,尤其是北方地区,各有特点,又整体趋同,整个发展呈现出多中心一体的特点。
第一次玉文化发展高峰的重心在南方,发展时间长、遗址分布广、数量多、影响深远。第二次的重心在北方,发展时间短,但是规模大,影响范围广泛。
在第一次发展高峰,红山文化位于北方燕辽地区,凌家滩、良渚文化位于南方长江下游地区,虽各有特点,但是整个玉器发展的重心是在南方地区。首先从出土玉器的数量就能窥其一斑。经考古调查、发掘、征集、采集的红山文化玉器数量约有355件[16],再加上一些散落于国内外博物馆和私人藏家手中的玉器,总数量应该不会超过千件。凌家滩遗址从1989—2016年5次发掘出土玉器就有千余件[17]。良渚文化玉器数量超过万件[18],是其他文化的数十倍之巨。其次再看出土玉器的遗址分布情况,红山文化玉器主要集中在赤峰和朝阳地区[19],主要是牛河梁、东山嘴、胡头沟等墓葬和遗址的出土品,和敖汉旗、巴林右旗、翁牛特旗等地的征集采集品,其余地点数量很少。凌家滩文化玉器主要出土于凌家滩遗址。良渚文化玉器出土地点多、数量大、分布范围较广,出土玉器的遗址点超过60处,分布范围主要在江苏、浙江和上海三地[20]。再次从玉器的流行时间看,三个玉文化的发展阶段延续千年,在距今5300—4300年间,玉器得到不断的发展,尤其是良渚文化,在其消亡的数百年后,在广东、甘青、陕北、晋南等地的遗址中仍能发现具有良渚文化特征的玉琮、玉璧等,足见其深远影响。因此无论是从遗址的数量、出土玉器的数量,还是出土玉器遗址的分布情况、玉文化的延续时间,南方发展时间长、规模大、数量种类丰富,是第一次玉文化发展高峰的重心地区。
第二次发展高峰的重心在北方地区。第二次发展高峰中的5个玉文化中心,除了后石家河文化(肖家屋脊文化),其余4个中心都位于北方地区。首先从制玉、用玉的中心分布看,北方地区就显得尤其重要。其次再看出土玉器的数量,晋南地区仅陶寺墓地出土玉器就超过500件[21],下靳墓地出土玉器近200件[22],另外清凉寺墓地出土玉器200余件[23],这些数量还不包括绿松石饰品、饰片。齐家文化玉器的出土数量据不完全统计,约3500件[24],石峁遗址玉器出土数量也应在3000~4000件[25],甚或更多。山东龙山文化出土玉器较为集中,数量也稍少一些,应该在100余件。后石家河文化(肖家屋脊文化)各地点出土玉器的数量据不完全统计有600余件[26]。简单从数量和规模看,在第二次高峰时期,北方都是玉文化发展的重心。而且在此之后,北方地区的牙璋、带领璧、玉璧等玉文化因素,夏商时期在闽粤、香港地区的普宁龟山[27]、平宝山[28],深圳黄竹园沙丘[29]、向南村[30],香港东湾仔[31]、大湾[32]等遗址中均有发现,在越南冯原文化中玉璋与玉璧是代表性玉器种类[33],是第二次玉文化高峰中以北方地区为重心的玉文化发展的外渐[34],体现出其影响的广远。
第一次玉文化发展高峰中建立了礼玉系统,推动了信仰体系的建立与认同;第二次发展中形成了礼仪制度,推动了文化整合,整合统一了黄河流域的玉文化面貌。
第一次发展高峰中,南北方玉文化发展有着密切联系,相互影响,并且差异较小。良渚文化玉器作为这一阶段的集大成者,发展出具有自身特色的礼仪系统。良渚文化社会是被玉器表述出来的社会,玉器表述出六个级别的墓地或可简称家族,区分出四大等级的人群,形成一个塔形的社会结构[35]。玉器作为等级标识,彰显着文化内聚落群间、聚落群内、不同家族、同一家族内人群的等级差异以及性别差异[36]。以钺、琮、璧及复杂玉头饰等为代表的礼玉种类,其上琢刻神人兽面纹,体现出良渚文化玉器在原始宗教或信仰体系中逐渐增加了礼仪的内容。明晰的用玉等级差异背后,是玉器所蕴含的用玉礼仪系统,也即礼玉系统,通过玉器来传达和表达等级和信仰系统的体系,是礼仪与宗教信仰结合的产物。良渚文明是玉器文明,是玉礼制文明,在整个良渚文化分布区有着广泛的认同,玉礼器系统的礼制和观念成为维系良渚社会政权组织的主要手段和纽带[37]。良渚文化通过建立礼玉系统,将玉器所蕴含的信仰体系推广到更大范围,更广区域。
第二次发展高峰中,南北方玉文化差异加剧,形成不同的发展模式[38]。南方地区玉文化的发展以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玉石器传统为基础,融合本地文化因素,玉文化的发展呈现出独立性的特点,走的是延续传统、独立发展的发展模式。北方地区玉文化以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玉石器传统为基础,融合各时间段多地区多种玉石器文化因素,各玉文化间频繁互动,玉文化的发展呈现出趋同的特点,走的是兼容并蓄、融合统一的发展模式。
南方地区主要承继了礼玉系统中玉器蕴含的原始宗教与信仰的观念,融合良渚文化中对神人或祖人图像的崇尚和相对比较完善的宗教体系,将日月鸟兽图像崇拜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吸纳本土文化及良渚文化中的神秘造型、纹样及其蕴含的观念,不断地开创新工艺,使得蕴含宗教与信仰观念的器物造型复杂化、神秘化,以彰显持有这类神徽类玉器人群的特殊性。北方地区主要承继了良渚文化建立起来的礼仪观念,在璧钺为基础的礼玉系统的基础上,吸纳与整合各时期各区域的玉石器文化因素,取之并入自身的礼仪系统,并根据自身需求创造出新的器形来完善礼玉系统,摈弃早期玉文化中对图像、图案的重点刻划,也即对神人或祖人的崇拜内容,以简洁、利落的几何造型器物组建新的礼玉系统。通过频繁的交流互动,最终以主体为钺、铲(圭)、璋、刀等长条端刃器,璧环等圜形器的礼玉系统为媒介建立起来的礼仪制度,整合统一了黄河流域的玉文化面貌。
第一次玉器发展高峰中,礼玉系统服务的是以神权为主导的社会,玉器是核心载体与媒介。第二次玉器发展高峰中,礼玉系统服务的是以王权为主导的社会,玉器只是其中一种载体与媒介,礼仪系统更为完备。
在第一次玉器发展高峰中,玉器与观念信仰和萨满式的宗教有关,在以神权为纽带的文明模式中具有绝对权威地位。统治阶层通过玉器及其背后的礼仪系统,达到对神权的控制,完成对王权、军权和财权的垄断[39];通过对玉器资源的控制,维系中心地位,来保持对周边聚落群的控制[40]。玉器是当时社会等级、身份的最主要标识,因此玉器是最能反映出遗址等级、人群等级的器物。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中墓葬以玉为葬,只有个别墓葬中随葬有零星陶器。良渚文化中遗址、人群等级皆以玉器为主要区分标准。
在第二次玉器发展高峰中,在发展的重心北方地区,反映宗教信仰和宇宙观的玉琮被改造、被弱化,具有神权意义的祖先图像被摈弃,在重世俗、重管理[41]的文明模式中,反映等级与权力的器物不是单一的,而是组合的,玉器只是其中的一种载体或者媒介。以陶寺墓地为例[42],早期高等级大型墓葬中一般随葬成套的石质工具、实用陶器、漆木器及乐器等;中期大型墓葬中一般随葬成套的彩绘陶器、漆器及玉器等,玉器在随葬品中的等级象征并不突出。而且同时期黄河上游和下游地区的高等级墓葬中还流行随葬猪下颌骨,另外鳄鱼骨板也是最高等级的指征物[43]。从这一阶段各文化墓葬情况看,成组陶器(彩绘陶、蛋壳陶、白陶)、漆器、乐器(鼍鼓、鼓)、成组猪下颌骨等组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宴饮组合,与玉器一并成为新的礼器系统。而且玉器的使用语境得到了拓展[44],从墓葬到祭祀,涉及到礼仪生活的方方面面。南方地区的后石家河文化核心区域石家河遗址各地点中,仍以神权为主导,玉器主要出自瓮棺葬中,还有玉敛葬的遗风,但是器形较小,可能多为佩饰。在其他地点中,玉器只是其中一类随葬品,数量也很有限,而且多为残件[45]。但是在宗教遗址周边,尚未发现玉器,而是出土了数量巨大的陶缸(筒形器)、陶杯、各类陶塑动物、陶偶等,可见玉器在社会活动和宗教活动中可能并非单一或具有绝对地位的象征物。
距今4300年前后,从大汶口晚期就开始的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乃至更大范围内文化面貌趋同的龙山化过程中[46],玉文化的发展表现出新的态势。
这一阶段,在没有用玉传统的晋南、陕北、甘青、长江中游地区出现了数个用玉、制玉的文化中心,这些中心在同一时间段内并行发展,相互影响,难分伯仲。在第一次玉文化发展中建立起来的信仰体系的基础上,文化进一步整合,并形成了礼仪制度。玉文化发展的重心由南方转移至北方地区,南北方表现出不同的发展模式。北方地区各玉文化通过频繁又深入的互动,在文化因素上表现出多元性、复杂性与综合性,但是在玉文化整体面貌上表现出趋同性、一致性与一体化,是多元性与统一性的结合。这些是北方地区这一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不同信仰、不同生业模式的各部族、人群间文化汇聚与认同的映射,是文化上整合的表现。正是在这种整合与认同的基础上,随即在中原地区孕育出现了国家,开启了中国历史新的阶段——王朝阶段[47]。同一时期的南方玉文化继续保持传统,表现出独特性和独立性,更倾向于输出而非吸纳、融合。在这样的文化传统与背景下,南方地区虽然在很长时间拥有发达的发展中心,对北方地区也有着深刻的影响,但是却始终未能发展形成地域性王国。
诚然,文明进程是个漫长又复杂的过程,通过单一种类的器物,不可能了解它的全貌。但是玉器作为高层次高等级的文化与意识形态载体、精神世界的象征,是一个人群宇宙观、世界观的体现,是文明进程与社会复杂化的见证。新石器时代玉器玉文化发展的两次高峰,一次见证了古国的形成与发展,另一次孕育了王国的形成,两次玉文化发展高峰构成了玉器时代的主要内容。正是通过这两次的发展,尤其是第二次高峰阶段的发展,统一了中华文化圈内玉文化的整体面貌,整合了玉器制作工艺技术,接纳了各类玉器所蕴含的深刻意义,奠定了中国玉器玉文化的发展趋势。从此以后,无论是王朝阶段还是帝国阶段,无论哪个部族主导政权,无论新增什么样的器类、纹样如何变化,无论玉文化的因素如何多元,从玉文化的整体面貌上看,中华文化圈都展现出统一性、一致性的特点。
在第二次玉文化发展高峰之后,随着中原地区对集体运作和公共事务的重视,文化和社会发展世俗化的发展趋势,在新的发达文明形态中,宴饮礼制传统逐步确立[48],随着社会上层贵族对更大范围、更广区域更多的珍稀资源的控制,社会资源控制体系的建立,龙山时代跨区域互动网络的形成与发展[49],玉器不再是唯一的珍稀资源,随着铜器的广泛使用,玉器的突出地位有所减弱,与新的文明形态同时发展起来的是下一个新的时代——青铜时代。
参考文献:
[1]赵辉.“古国时代”[J].华夏考古,2020(6);赵辉.谈谈“古国时代”[J].文物天地,2021(5).
[2]严文明.龙山文化和龙山时代[J].文物,1981(6);张弛.龙山—二里头——中国史前文化格局的改变与青铜时代全球化的形成[J].文物,2017(6);赵辉.“古国时代”[J].华夏考古,2020(6);张弛.龙山化、龙山时期与龙山时代——重读《龙山文化和龙山时代》[J].南方文物,2021(1);赵辉.谈谈“古国时代”[J].文物天地,2021(5);张海.“龙山时代”: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关键时段[N].学习时报,2021-1-1;张海,赵晓军.仰韶与龙山之间:公元前3千纪前半叶中原社会的变革[J].中原文物,2021(6).
[3][38]杨岐黄.4300年前后玉文化发展的南北模式[J].待刊.
[4][44]秦岭.龙山文化玉器和龙山时代[C]//考古学研究(十五)——庆祝严文明先生九十寿辰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22:488-546.
[5]朔知.从凌家滩文化看中国文明的起源[J].安徽史学,2000(3);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凌家滩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之一[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278.
[6]张星德.红山文化分期初探[J].考古,1991(8);赵宾福,薛振华.以陶器为视角的红山文化发展阶段研究[J].考古学报,2012(1);刘国祥.红山文化研究[D].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15:18-19;周晓晶.红山文化玉器研究[D].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41-70;冯玉雪.“玉龙故乡”发现更早的“龙”[N].内蒙古日报,2021-8-21.红山文化的玉器流行于红山文化晚期阶段,大致距今5500—5000年。2023年在内蒙赤峰彩陶坡遗址发现了红山文化偏早时期的蚌龙造型,为早期阶段存在成熟玉器提供了可能性,红山文化玉器的时代很可能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展开,会有所提前。
[7]刘越,吴卫红.长江下游史前文化格局与文化特质的形成[J].中国文化研究,2022(3).
[8]艾江涛.凌家滩:充满创新活力的治玉中心[J].三联生活周刊,2023(20).
[9]张光直.古代中国考古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李新伟.中国史前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网的形成[J].文物,2015(4);李旻.天下之九州:龙山社会与龙山世界[C]//考古学研究(十五)——庆祝严文明先生九十寿辰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22:330-350.
[10]传统认识中,龙山文化的年代上限为距今4600或4500年左右,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起始年代有所延后,在距今4300年前后。近些年禹会、平粮台等遗址的测年数据显示在距今4400—4300年之间,但是鉴于各序列的测年数据尚未同步、统一,本文仍以探源工程的认识为准。
[11]中国社会科学院,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襄汾陶寺——1978-1985年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何努,严志斌,宋建忠.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中期墓葬[J].考古,2003(9).遗址领队高江涛先生提及,最新考古测年资料反映出,遗址的上限应该可以到距今4400年前后。近些年在周家庄遗址的工作将晋南龙山文化的下限年代也推后到距今3750年左右。本文讨论内容以陶寺遗址为主体,因此使用陶寺遗址陶寺文化的年代范围。
[12]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史前考古研究室.2008-2017陕西史前考古综述[J].考古与文物,2018(4);孙周勇,邵晶,邸楠.石峁文化的命名、范围及年代[J].考古,2020(8).
[13]闫亚林.西北地区史前玉器研究[D].北京大学学位论文,2012;张天恩.齐家文化对中原地区文化的影响[C]//齐家文化与华夏文明研讨会论文汇编.2014.
[14]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天门市博物馆.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2014-2016年的勘探与发掘[J].考古,2017(7);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文物局.湖南澧县孙家岗遗址2016年发掘简报[J].江汉考古,2018(3);张海.“后石家河文化”来源的再探讨[J].江汉考古,2021(6).湖北石家河遗址发掘简报中的测年数据基本为距今4200—3800年,位于湖南的孙家岗遗址的测年数据能早到距今4250年前后。
[15]杨岐黄.4300年前后玉文化在北方地区各文化间的互动[J].考古与文物,2020(2).
[16][19]周晓晶.红山文化玉器研究[D].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
[17]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含山凌家滩新石器时代墓地发掘简报[J].文物,1989(5);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含山县凌家滩遗址第三次发掘简报[J].考古,1999(1);凌家滩遗址考古队,安徽大学,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含山县凌家滩遗址第四次发掘简报[J].东南文化,2021(5);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含山县凌家滩遗址第五次发掘的新发现[J].考古,2008(3);吴卫红.安徽含山县凌家滩遗址新石器时代墓葬的清理[J].考古,2020(11);杜佳佳.凌家滩玉器的考古学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6.
[18][20]汪遵国.良渚文化玉器丛谈[C]//长江文化论丛(第一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70-88;王明达.古国惊梦玉魂国魄:良渚文化考古亲历记[J].东方收藏,2011(1).
[21]中国社会科学院,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襄汾陶寺——1978-1985年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报告中玉石器数量900余件,但是其中有些器类如磬、镞、研磨盘棒等应归入石器,有些器类如钺、璧等是玉石兼用,鉴于当时玉料的稀缺性,一并归入玉器。如此,陶寺墓地出土玉器的数量约有500余件。
[22]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山西博物院.下靳史前墓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
[23]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运城市文物工作站,芮城县旅游文物局.清凉寺史前墓地[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
[24]王裕昌.甘肃省馆藏齐家文化玉器调查与研究[C]//2015中国·广河齐家文化与华夏文明国际研讨会.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203-216.
[25]戴应新.我与石峁龙山文化玉器[C]//中国玉文化玉学论丛续编.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4;孙周勇,邵晶.关于石峁玉器出土背景的几个问题[C]//玉魄国魂——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六).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
[26]荆州博物馆.石家河文化玉器[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张溯,申超.后石家河文化玉器的初步研究[C]//海岱考古(第十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陈茜.石家河文化玉器研究[D].湖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天门市博物馆.石家河遗珍——谭家岭出土玉器精粹[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
[27]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普宁市博物馆.广东普宁龟山先秦遗址2009年的发掘[J].文物,2012(2).
[28]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岭外遗珍——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基建考古成果选萃[M].广州:广东省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39-40.
[29]深圳市博物馆等.广东深圳市盐田区黄竹园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2008(10).
[30]深圳市文管会办公室,深圳市博物馆,黄山区文管会办公室.深圳市南山向南村遗址的发掘[J].考古,1997(6).
[31]香港古物古迹办事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香港马湾岛东湾仔北史前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1999(6).
[32]区家发,冯永驱等.香港南丫岛大湾遗址发掘简报[C]//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195-208.
[33]Ha Van tan. Yazhang in Viet Nam[C]//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庆祝郑德坤教授从事学术活动六十周年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451-454.
[34]张强禄.从华南所见有领璧环看夏商礼制东渐[C]//古代文明(第13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57-91.
[35]张忠培.良渚文化墓地与其表述的文明社会[J].考古学报,2012(4).
[36]宋建.良渚文化的用玉与等级[C]//上海博物馆集刊.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8:371-382;徐鹏飞.良渚文化墓葬及其反映的社会结构与形态[J].国家博物馆馆刊,2015(3);方向明.良渚玉早期中国文明模式[C]//考古学研究(十五)——庆祝严文明先生九十寿辰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22:229-249.
[37]方向明.良渚玉早期中国文明模式[C]//考古学研究(十五)——庆祝严文明先生九十寿辰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22:229-249.
[39]刘斌等.良渚:神王之国[J].中国文化遗产,2017(3).
[40]郭明建.良渚文化宏观聚落研究[J].考古学报,2014(1).
[41][48]张海,赵晓军.仰韶与龙山之间:公元前3千纪前半叶中原社会的变革[J].中原文物,2021(6).
[42]中国社会科学院,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襄汾陶寺——1978-1985年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
[43]孙丹.中国史前墓葬随葬猪下颌骨习俗研究[D].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学位论文,2013.
[45]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博物馆.湖南澧县孙家岗遗址墓地2016-2018年发掘简报[J].考古,2020(6).
[46]张弛.龙山化、龙山时期与龙山时代——重读《龙山文化和龙山时代》[J].南方文物,2021(1).
[47]赵辉.谈谈“古国时代”[J].文物天地,2021(5).
[49]李旻.天下之九州:龙山社会与龙山世界[C]//考古学研究(十五)——庆祝严文明先生九十寿辰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22:330-350.
作者:杨岐黄(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原文刊于:《中原文物》 2024年 第1期
文章来源: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 公众号 链接:杨岐黄 | 距今4300年前后玉文化发展的新态势——从新石器时代两次玉文化发展高峰入手 (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