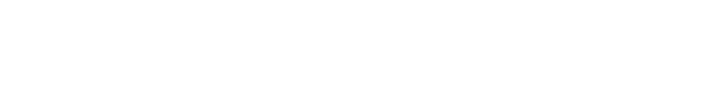葛承雍 | 驿路寺城:新疆奇台唐朝墩古城考古的新认识
唐城墩住宅院落(考古队无人机摄)
内容摘要
本文针对新疆奇台唐朝墩近年考古成果做了分析,认为唐朝墩作为蒲类县古城遗址,实际就是丝绸之路上一个驿站群组成的“蒲类津”县城,景教、佛教寺院和浴场环环相扣,都是伴随着驿站建立的配套宗教建筑,宗教信仰场所便于旅途匆匆来往人群有所依傍,便于停靠与补给。服务于商客、官员、使节等类似的驿站城镇遍布中亚至西域,但是随着战争破坏和时代变迁保留下来的很少,因而唐朝墩重大发现属于丝绸之路链条上重要一环,不仅有着边疆考古学术示范作用,而且有着助解西域中古谜团的典型意义。
根据世界遗产城市组织(OWHC)的阐述,从中亚到西域的历史城市总数大概达到了五百座,它们串联了各处贸易市场、宗教圣地、驿站邸店,发挥了交通枢纽的联系作用,起到了文化交流的网络作用。创建于贞观十四年(640)的庭州蒲类县(清朝称为唐朝墩),沿用到14世纪蒙元这样区域中心下的城镇不一而足。但在各种战乱冲击和自然毁灭下,废墟较为普遍,能完整保留下来的非常罕见[1]。
唐朝墩位于新疆奇台县城东北部,西距北庭都护府遗址直线约30公里,南距汉代疏勒城遗址约40公里,地处准噶尔盆地东南缘和天山北麓的狭长东西通道上,有其在天山北麓优越的地理位置,按照中古波斯“王道”两个驿站之间商贸驼队一天行程20公里,从北庭到奇台需要两天。正是路网在古代交通繁忙背景下造就了一个个驿站旅舍(邸店)群,汉唐元明历史时期下,驿站群和旅舍群发挥着得天独厚的重要作用,驿站旅舍不仅是一个温暖而诗意的词语,而且形成了独特的“古城”群聚文化。在丝绸之路交通路网研究中,“驿站”“旅舍”“邸店”“车马铺”等是必不可少的首要选题,更是古城考古不应忽视的重点关注对象。
驿站是古代专供官府人员休息和军队行军途中食宿、换马的场所。旅舍则是商人、民众歇脚补给的食料物质补给站。奇台作为丝路新疆北线的中枢,周围有许多驿站,《新疆图志》卷七九记录的屏营驿,在奇台县旧治靖宁城,今奇台县老奇台镇。奇台县半截沟镇腰站子村,就是原来“四十里驿站”。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政府在今老奇台设奇台堡,四十里腰站子因地近四十里铺而得名。这些都记录着千年以来的风貌变化。唐朝墩古城遗址东西宽约341米,南北长约465米,按唐代里程换算,即东西220步、南北300步,约合唐代一坊之大小。县城常常位于主道、河流、山口等重要地段,配备的防御设施能控制交通要道、水源灌溉等线性分布。唐朝著名诗人骆宾王投笔从戎,出玉门关随军赴轮台就写有《夕次蒲类津》诗[2],“蒲类津”作为边塞关津是当时来往西域的必经之地。
我们要从整个唐代蒲类县古城布局来考虑,以整体思路从驿站角度切入,就是官府县衙、驿站邸店、佛寺位置、教堂建筑、浴场濒河、商铺货栈及民宅院楼等综合思考,但它可能不是按照中原筑城法则或模式建造的城池,而是要进一步从跨文化角度考虑古代商路上的宗教礼拜地、补给仓储地、商贸交换地,研究7—12世纪几百年间这个古城的发展变化。中亚有些城市以商贸圈结合驿站群形成古道上的网络,虽然这类城市布局不大,但城墙环绕下的大街小巷有条不紊。有了聚落人群与往来商客,就伴随着有了宗教信仰的传播,这样在剖析宗教精神遗产概念的基础上,我们研讨景教教堂和修道院的关系,观察佛寺的交错布置,通过考古多角度视野考虑建筑史、宗教史、人类学等多重价值,为中世纪的身份认同和信仰地区差异提供新的认识。
一、对景教寺院的认识
土耳其以弗所(Ephesus)曾是基督教东方教会的一个大本营,景教聂斯托利派在此分裂向东传播。以弗所作为一个原来海陆交通枢纽城市,就是罗马浴场式在东方的一个典型代表,棉花堡修建于2000多年前的阿佛洛狄西亚(Aphrodisias)卫城,至今残存着希腊风格的澡堂、拱门、横梁、石柱长廊、殿堂式大理石柱,它们全部由雪白的大理石雕筑而成,花纹繁复,造型宏伟。
借鉴以弗所交通城市的经验,我们再思考2019年发掘唐蒲类县即奇台唐朝墩的布局,尤其是关注到景教寺院居于城中的位置,可见其在当地的重要位置和宗教印象。中亚的宗教建筑通常坐落在主要的行政中心附近,从花剌子模到撒马尔罕都是如此,不仅宗教生活多在社群高密度层面进行,而且显示宗教生活在当地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这种城市布局很有可能是官府策划和动用府库投资修建的。
花剌子模梅尔夫(Merv)在公元651年被阿拉伯人征服前,起源于5-6世纪的教堂一直使用到11 -12世纪,考古发现用泥砖建造的矩形形状教堂,圆筒形穹顶已经毁掉,实测约51米长,13米宽,萨珊波斯末代君主伊嗣俟(Yazdegerd)于公元651年死于梅尔夫附近一个磨坊主手中,就是由这个城市的景教主教埋葬的。中亚的教堂大多是纵向的有拱顶的建筑,圆筒形穹隆,由于大多是用泥砖或土坯建造的,因而往往只有一个中殿,多是三跨的结构,很少有四跨五跨的,与亚美尼亚石构教堂规模巍峨相比还有相当差距。
粟特地区阿夫拉西阿卜作为一个重要游牧贸易中心,在5到7世纪期间,阿夫拉西阿卜一直是一个重要的游牧贸易中心,在5到7世纪期间,它不仅是一个主教辖区的所在地,而且之后是聂斯托利派大主教席位所在地。在乌尔古特(Urgut)、片治肯特等地经过考古发掘都发现存在聂斯托利派教堂,在一个花瓶的碎片上发现了圣经中的《诗篇》第一篇和第二篇的两段摘录,是用叙利亚语写的。片治肯特壁画的组合被证明是一个极其融合的世界,中亚的绘画和雕塑都很好地表现强调了当地社会的民族多样性,也是多种宗教的传教倾向及其反映。在哈萨克斯坦七河地区塔拉兹考古中,发现7-8世纪的地层中有带有叙利亚文和粟特文的具有基督教意义的铭文的花瓶碎片。
我们再看碎叶城,1953年,以俄罗斯考古学家克兹拉索夫(I. L. Kyzlasov)为首的楚河流域考古调查分队(Cuyskiyarheologiceskiyotryad)再次对阿克·贝希姆进行了大规模挖掘,在此挖掘出一处摩尼教墓地、一座景教教堂、一座火祆寺“寂静之塔”及一座奇迹般保存完好的佛教寺庙遗址,并同时出土了一批铜鎏金佛像残片、佛寺壁画残片、泥塑佛像残片以及一组12件工艺精美的镂空鎏金佛教图像铜牌饰与6枚粟特神像的铜牌饰。碎叶一共发现了三座佛寺,据推测有武则天时代的大云寺,这说明佛教徒对景教及其他宗教持宽容态度。事实上几种宗教互不攻击经历了一段新的繁荣时期,一直持续到14世纪末[3]。
图1,新疆奇台县唐城墩古城平面图(采自考古展览图)
景教在会昌五年灭佛劫难中被撤出中国内地,但在西域被保留直到元代也里可温。奇台的景教寺院如果是唐朝就建立的,或许在6-7世纪隋唐之际就已经存在(图一)。遗憾的是,目前没有景教文本文献被发现,或许当时教徒与传教士交流通过口头实现布道更多些。但是发现的壁画题材既有与佛教相似的供养人、祥瑞纹样等内容,也有独具景教特色的十字架、权杖等元素,还有回鹘文“也里可温”榜题,这应该是中亚景教东渐延伸的证据[4]。
中国的景教寺院遗址曾在西安周至大秦寺、内蒙古达茂旗敖伦苏木古城、河北沽源梳妆楼、北京房山十字寺等地发现过,作为新疆地区景教曾在喀什噶尔建立了包括七河地区在内的总主教教区。七河地区还曾发现两座聂斯托利教徒墓园。吐鲁番西旁的景教遗址推测是修道院[5],周至大秦寺遗址其实也是修道院。而比较完整的景教寺院遗址无疑是唐朝墩古城新的发现。
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阿克·贝希姆废城)碎叶城的景教寺院遗址我考察过,发现的教堂建筑遗址要比奇台的大。碎叶城遗址在90年中期后又发现一座景教寺院,可能包括3座教堂,包括修道院,每个区有一座主题建筑-圣堂,其中A、B、C建筑是教堂,B、C、D发现有厨房和图书馆,此外还有其出土的两个酒瓮,特别是小型酿造葡萄酒设备很令人惊奇。葡萄酒作坊,圣徒陵墓,但无洗礼池。
图2,亚洲景教寺院分布图
唐朝墩景教寺院出土了玛瑙、绿松石、玉石、琥珀等不同质地的珠饰,有可能是教徒供养留下的遗物,也有可能是信仰景教的商客敬献的贡物,关键是墙壁民族文字和壁画图像的解读,需要多方考释,破译后找出合理的答案(图二)。此外,骑马带背光的人物图,究竟是圣像图还是主教图,只有拼接大些图像才可辨别。现在出土的虔诚信徒图像也成为人们心中标准的版本,景教区主教和信徒们只有笃定了自己的信仰,才能毅然决然地前往周边各地宣传福音。壁画的出现是景教传教士和信徒互动的重要标志,当地应该有一定数量的景教信仰者。
图3,奇台唐城墩景教寺院俯瞰图
考古队将在2023年继续发掘景教遗址的东部,因为这是居住区,有很多房址,出土有青铜十字架、鎏金铜像等。究竟是修道院还是供基督教商人住宿,有待遗物的进一步考证(图三)。这也促进我们进一步思考当时景寺的经济支撑问题,其背后有一定强大的财力、物力和人力的支持,究竟是来往商旅捐助或是官衙用税费支持,笔者怀疑有当地政府经济支持,否则单靠景寺自己很难支撑下去,自发延续几百年会很艰难的存在。
景教寺院遗址发现的几口井,值得关注,是否有圣人骸骨、宗教圣器、酿酒设施等,如果我们联系吐鲁番高昌绘有基督教主题壁画的建筑,以及出土的文书,将会对西域的景教研究继续推动。
二、对佛教寺院的认识
佛教在西域是一个影响重大的宗教,佛教寺院遗址发现的也很多,往往依托古城存在。3世纪至8世纪在西域多元文化融汇背景下,佛教与其他宗教的关系值得关注,唐朝墩古城内景教教堂与佛教寺院这么近距离的存在,估计当时蒲类城中居民不会太多,竞相布教争夺信徒和供养人捐助,会不会出现矛盾纠纷,会不会妥协调和、和睦相亲,双方共拜不同的神祇,神学却共同生活在这么近距离的城中,是否证明双方修好公平共处呢?或许是粟特胡人的佛寺和回鹘的也里可温容易沟通相安,而且中唐以后这里多民族轮番上演执政统辖的局面,军事对抗角逐激烈,中外僧侣穿梭其间,借助宗教的力量可能会使摩擦缓和。放眼亚洲和中国,景教祆教摩尼教“三夷教”的传播和影响扩张,都会遇到这类问题。但从中原内地来看,还是佛教力量最强。
图4,唐城墩景寺正面(以下作者拍摄不再注明)
现在发掘的佛寺遗址有佛塔基座和佛像出土(图四),佛寺遗址由围墙、回廊、塔基地宫、佛殿、前庭和前院等6个部分构成,出土遗物以陶器为主,并有部分石器、瓷器、骨器和金属器,其中的佛造像和莲花纹瓦当较为显著地反映了当时佛教的艺术特点[6]。佛教建筑与景教遗址共存的现象,在各个大小城市均出现过,除了长安、洛阳等外,一些中亚绿洲小型定居城镇也有,8世纪萨珊波斯和西突厥影响的地区,佛教寺院与祆教火坛遗迹均有共存。尤其是各个政权联盟反复争夺地域,造成多元宗教并立的局面,例如蒲类古城暂时无法知晓更多细节,但是出土壁画上有供养人画像(图五),由此依据考古发现可做粟特、回鹘、突厥、汉人等多种人群汇聚的推测。
图5,景寺正殿侧面
佛教每年“浴佛”活动成为各地风俗,唐僧义净介绍“西国人多洗沐,体尚清净”。每天不洗不食,驿站旁穿池为福,那烂陀寺就有十余所大池。沐浴习俗传入中国,长安诸寺有浴。唐朝墩古城的浴场很可能也是为佛教僧侣和信徒服务的。佛经中记载佛陀曾亲自为生病的比丘洗浴,因为洗澡能除七种病,得七种福。因此,佛教传入中国后,各地在创建寺院时,大都仿印度风习而设立浴室(释迦丛林中,浴室乃七堂伽蓝之一,并设有知浴、浴头等职役),很注重信众弘法参拜时的设施。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唐宋时代在寺院道观里置有官舍,按照《新唐书》记载,“天下僧尼、道士、女官,皆隶鸿胪寺”,外交主管部门鸿胪寺还管理僧尼,寺院客房兼具官方驿站的功能,唐代佛教官寺的特殊功能之一就是接待外国入华僧众和国内往返客官(包括家眷),官寺规模比一般小寺兰若大,戒律严明,设施较好,能代表官府形象。同时还能借官寺监控来往行客行踪,充分具有官驿的职能[7]。据日本入唐求法僧圆仁记载开成五年(840)在唐境途径登州都督府城,有开元寺、法照寺、龙兴寺,其下蓬莱县开元寺“僧房稍多,尽安置官客,无闲房,有僧人来,无处安置”[8]。唐代往往是领民四万户的“上州”才设立大官寺,像蒲类县这样庭州管辖下的县所,可能作为一个特殊的驿站、官寺和外来宗教传播所在地,因此,我们综合观察蒲类县(奇台)的遗址布局,很有可能是一个多功能作用的汇聚之地。
从宗教艺术角度来看,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寺院壁画上新元素,特别是有人物形象的遗迹残片和雕塑,依此分析当地画匠、画师们的创作与中原寺院的异同。不管是什么宗教,其视觉图像的一个优点就在于它比晦涩难懂的文字更有表现力,一样都具有阅读价值,对不识字的信徒来说尤其如此。绘画和雕塑在提供教导和训诫上的重要性不亚于任何书面文本,在塑造信徒的道德理解力上起到了独特的作用,被称为“无言之教”(mutapraedicatio,preachingwithoutwords),壁画形象频繁出现在教堂建筑图像领域中,这对于无法直接阅读多种语言文本的信徒去理解和接受信仰教训尤为重要。
如果蒲类古城沿用到元代,伊斯兰教是否传入到天山北道,穆斯林在这里是否建有清真寺进行礼拜,元代伊斯兰教已经在沿海泉州建有清净寺,但在北方特别是西域地区一直未有定论,这次在奇台古城墩景教遗址上面发现一个陶罐,上面有阿拉伯文或波斯文“基督”之类的文字,通过宗教痕迹,说明穆斯林东渐伊斯兰化过程是漫长的。
图6,寺院墙壁上回鹘文也里可温字样
我注意的是佛寺回鹘文榜题,可能记录有高昌回鹘统治阶层名称。唐朝墩佛寺遗址整体揭取壁画3幅,为高昌回鹘时期绘制,均位于佛台北侧的壁面之上。其中底部墙面揭取的壁画内容最为清晰,画面宽约140厘米,高约40厘米。壁画以黑色线条并排绘制5个供养人形象(图六),由于墙体坍塌破坏,仅残存人物下半身,均朝向东侧,着开襟滚边长袍、尖头长靴,中央的供养人形象衣袍着红彩。各供养人右侧方框内均有墨书回鹘文榜题,应为供养人的姓名。如果像殷小平教授判断的唐代景教徒以伊朗语系的波斯、粟特裔教徒为主,蒙元时代的也里可温主要为突厥语系族群。那么回鹘景教、佛教作为几百年间重要中间环节,壁画和榜题上都可能是突厥裔的文化烙印[9]。
三、对浴场考古的认识
1982年至1995年西安临潼华清池遗址历时14年考古发掘,是我国第一次对大型浴场建筑的发掘,这次奇台县唐城墩浴场是第二次通过考古发现的较完整浴场建筑(图七)。华清池浴场是唐代皇家温泉浴场,在墨玉石、白玉石等石构建筑技术方面可能吸收过罗马浴场的元素。而唐朝墩浴场与罗马帝国范围内的浴场建设则可能有密切关系,因为浴场建筑采用烧火加热与罗马浴场建筑技术非常相似,分为热水池、温水池和冷水池,其梯级台阶的建筑形式和方法应该是罗马式的技术。但是我认为唐朝墩的浴场不可能像罗马帝国境内浴场那样规模宏大,很可能不适于众人洗浴的大池子,而是分隔房间有浴缸、浴盆之类设施,冷热水由管道供应,并用分水阀进行调节,在罗马和庞贝古城遗址中都有类似的发现[10]。
图7,景寺墙壁上人物画中的十字架
这是丝绸之路沿线浴场遗址的延伸线的一个节点,是驿站邸店建筑的附属物,由此判断,当时贸易商队和官家团队经过住宿时使用这个浴场(图八)。值得注意的是,浴场或浴室作为佛寺社会公益经常也为当地民众服务,石刻《法门寺浴室院灵异记》记载自唐僖宗乾符年间(875)至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百年间每日僧俗千人沐浴,除污疗疾未曾中断,这是寺院的福利善举之一,其规模不小,让信徒在沐浴中享受佛祖的恩典[11]。
图8,景教寺院墙壁上回鹘文
其实从罗马、印度、中亚等地的浴场来看,大浴场都有为宗教仪式服务的传统,它们利用水源导引水道系统以满足浴场的需要时,有“圣水”“圣泉”疗病的崇拜。例如1998年在哈萨克斯坦南部卡亚利克古城就发现毗邻广场浴场和摩尼教寺庙,属于11-12世纪西辽和蒙古察合台时代,有着浴场供水系统[12]。哈萨克斯坦塔拉兹城中世纪城堡的中央市场中有公共澡堂和琐罗亚斯德教火焰神殿[13]。外国学者专门著文指出“罗马浴场作为宗教活动的场所”,在浴场内部装饰往往有祈祷神灵或神话人物,人物肖像有时带有宗教纪念意义,或是驱魔功能[14]。唐朝墩浴场发现的人物壁画或许也有这方面的意义。现在发现唐朝墩浴场的壁画残片(图九),虽不清楚绘画内容,但是线条色彩清晰可见,说明当时浴场是有装饰的,浴场里面残存有壁画或其他艺术装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交流传播现象。
图9,景寺残存壁画
尤其是唐朝墩浴场建筑旁临水磨河西岸台地之坡下河道,其提水入浴的管道很重要,华清宫浴场的陶制管道曾遍布临潼县城,水系对浴场及其他场域的食、住、行生活都非常重要,是蒲类古城格局和聚落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进一步需要关注浴池建筑底部,要检测香料药物的“香汤”痕迹,推测浴场进水出水口的高架水道,浴场燃料来源及经济成本等等,并继续探讨浴疗的特殊性。
浴场考古全景图
浴场考古图之一
浴场考古图之二
浴场考古图之三
浴场地下火道
浴场考古现场之四
我曾在1996年写过《唐华清宫沐浴汤池建筑考述》和2006年《唐华清宫浴场遗址与欧亚文化传播之路》[15],当时寻找海内外浴场资料还有限,只是关注到道教、佛教对沐浴的重视,并不清楚基督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对沐浴也很重视,现在唐朝墩古城提供新的证据,说明沐浴建筑绝不是一种孤立的文明现象,各个宗教都对洁净洗身的沐浴非常重视。
再望远处延伸看,我们观察到伊朗的土耳其浴室为例。当年,奥斯曼帝国崛起后灭亡了东罗马,却将罗马式浴室文化发扬光大,奥斯曼和波斯双方打了几百年的仗,浴室文化却深得双方欢迎,奥斯曼没有灭掉波斯,土耳其浴却占领了故国,在波斯地区风靡一时。毕竟都是伊斯兰地区,净身对于他们来说,同等重要。
浴室在当时整个罗马演化到阿拉伯及波斯地区,承担着非同一般的社会角色,远不至洗澡那么简单。[16]土耳其浴室在促进卫生和公共健康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但它们也是人们放松和社交的聚会场所。除了洗澡、桑拿、按摩、刮胡、理发等等常规功能外,还有美食、交友、议事、亲友团聚、生意洽淡等各种功能,其实多是综合性的文化娱乐中心,他们往往早上进去,一直到日落才会回家。公共浴室(或称hammam)在任何中东城市都是一项重要的社会制度,中世纪时期,公共浴室已经成为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浴室的质量和数量是任何城市最令人钦佩的特征之一。
这种风习从地中海地区渗透到中亚,即是古罗马术语的“直系后裔(direct descendants)”。Afrasiab, Nisa, Tashkent, Taraz, Otrar, Kayalyk等遗址的考古发掘中也了发现浴场。在布哈拉和撒马尔罕都有浴场建筑,布哈拉在10世纪有许多浴场,其中最著名的是HammomKhon(“可汗的浴场”)。到19世纪中叶,浴池的数量从塔什干的11个增加到了16个,到20世纪初,撒马尔罕只有8个浴池。浴场根据其位置可分为两种类型:城市(巴扎Bazar)和街区(古扎Guzar)。巴扎浴场紧邻贸易区,许多中亚浴场都是单层圆顶建筑,布哈拉有许多这样的澡堂。哈萨克斯坦南部广泛存在这种类型的浴场,考古学家在塔拉兹、奥特拉尔和古丝绸之路上的其他城市的发现就证明了这一点(图十)。其实,新疆博尔塔拉的达勒特古城也曾发现过浴池建筑遗址,只不过没有考古简报发表。中亚到西域这种古城建筑布局,对我们理解似曾相识的奇台同类浴场文化很有启发。
图10,景寺人物壁画
据说,浴室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功能,就是相亲。伊斯兰国家的女子往往全身裹的严严实实,那些婆婆在找儿媳妇时,就会约上媒人及备选儿媳妇一起去澡堂,洗完澡后一边交流品尝自己做的美食,一边偷不溜的瞄瞄未来儿媳妇,那样对未业的儿媳妇的体态、容貌、体味、谈吐等关键信息就会准确无误一览无余。无论是大的浴池或是小的浴室,其功能确实多样的。
四、对丝路驿站聚落群的认识
我们现在还没有一部西域古城史,奇台无疑提供了一个经过考古实证的范例。唐代蒲类县治在今奇台唐朝墩古城,实距庭州以东、伊州以西诸城之冠,大于庭州之西的三台、滋泥泉、米泉、乌拉泊等古城,虽然蒲类县比不过庭州、昌吉古城,但在天山北道这个区域里应该是最重要的古城了,因而它才有空间条件和人口集中的前提建设这么大的浴场、景寺、佛寺等公共建筑。现在实测城址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东西宽约341米,南北长约465米,面积约16万平方米。通过残存的遗址,我们已经很难复原古代唐朝墩地面上的完整旧貌,但它不是边关城市,也许不是贸易集市聚集地,按照古代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制度,官置驿站应该是不少的,为过往使者、商队、军队提供交通工具和食宿,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来支持支撑,如果能发现驿站旅舍建筑遗址,无疑也是令人振奋的消息。
西域古城址往往沿着古代道路而分布,历代王朝不仅将驿站作为传递信息、递运物资的主要渠道,而且在维系政权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古道的通塞或迁改,政治与自然环境的变化必然造成古代城址的盛衰。过去寻觅古城往往都是与驿道走向互为前提。官道驿路与乡间小路有别,官道沿途带有铺、驿、堡、亭、塘、店名称后缀的村落和烽燧,与驿站费用、军饷支撑、财政摊派等等都密切相关。蒲类县在古代无疑是一个中西交通的节点,既是中继出发点,也是补给线的关键。例如县城东北20公里处的北道桥古城,是古代奇台通往蒙古的交通要塞,北临沙漠,南控平原,直到清前期还在使用。目前可考的吐虎玛克古城,唐朝圪垯,大西沟古城,靖宁城等都曾驻兵守关口,他们构成一个网路。
如果有条件,我们应该有规划持续加强奇台边界墙的发掘和聚落形态的研究,进一步探究其公共安全的防御体系,扩大揭露古城县治民居院落的遗址,是否有改建或扩建的证据,目前城中西北大型院落遗址内发现了多个袋形窖穴(图十一),出土了较多具有明显唐代风格特点的遗物,很有可能是官衙储藏库或驿站储备物资的遗址。我们需要进一步了解其是否有公共墓地和高等级墓的分布,对石塚、石人墓碑、石墓桩进一步调查发掘,从城市遗址角度总结出整个古城的文化面貌和遗存特征。
图11,景教寺院供养人壁画
图11-B,唐城墩景教寺出土残存壁画
笔者按照中亚许多古城考古发掘成果推测,奇台作为古丝路新北道上的交通枢纽和重要商埠,古城里的建筑大部分应该是货栈、商队旅社、市场与巴扎等,这样商贸街区才符合驿站聚落式城镇。据当地调查清末民初,计有大小商号690家,运来送往的驼队多达4万余峰,自古就有“千峰骆驼走奇台,百辆大车进古城”的说法。至清末时,奇台有不同规模的各省会馆12处,商埠驿站非常明确,所以这里不仅仅是只用来居住的区域,如果紧紧围绕驿站群主线,兼顾景观考古、地质地理、河流水系、交通道路、物流商贸、墓地葬俗、衣食住宅、建筑工艺材料、军事体系与城镇生活等学术成果,将会为讲述生动的奇台古城提供丰富资料。特别是八世纪中亚浴场建筑在驿站枢纽公共建筑中占据了显著位置,因为在居民的生活中,它扮演着主要角色之一,是仅次于宗教寺院的最受欢迎的地方。
图12,新波斯文基督徒釉陶罐
图13,佛寺遗址现场俯拍图(考古队供图)
图14,佛寺出土佛像
可以说,奇台作为一个丝绸之路上“设馆置驿”为多元文化特色的示范点,为研究西域古代文化遗产,既提供了新的驿站城镇证据,也为一个宗教之城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证据,如果我们进一步观察北庭都护府分布的附属“卫城”模式,就可更清楚看到奇台作为丝路驿站聚落的一个交通符号,一种路网中转枢纽象征,一半是驿站一半是寺院,几方的叠加似乎在长久地提醒我们,不仅有益于进一步研究西域宗教的文化价值,而且帮助我们勾画支撑着丝绸之路研究架构路网的图景。
图15,佛寺残存供养人壁画
注释:
[16]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等编:《庞贝:瞬间与永恒》第111页,文物出版社,2018年。
文章来源:《世界宗教研究》2024年第1期,丝路遗产 公众号 链接:驿路寺城:新疆奇台唐朝墩古城考古的新认识 (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