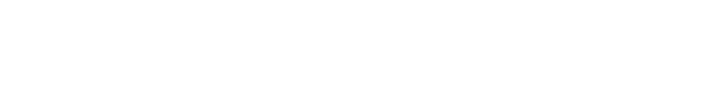刘庆柱 | 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考古学阐释
编者按:2023年6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了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与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与发展座谈会。在听取大家发言后,习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中华文明发展史中形成的五个“突出特性”,即“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本期特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郑州大学特聘教授刘庆柱先生撰稿,对考古发现与以往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结合出土文献与相关史料记载,阐释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形成、发展过程及其内在联系,并从世界古代文明史的视角,解读中华文明“五大特性”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摘要:中华文明发展过程中形成“五个特性”,其中“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是国家原则,“包容性”“和平性”是国民特性。中华文明“连续性”就是其国家历史的连续性,与其“国民”一代一代的延续不断裂发展,考古发现的出土文献与古籍典藏又共同进一步深化、佐证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史的“连续性”是基于其历史发展中的“创新性”,中华文明“统一性”首先通过对“中华文明”共同“祖先”——黄帝的祭祀体现出来、一代又一代传承。根据最新考古发现与遗传学研究成果,目前中国本土绝大部分人的基因与五六千年前的人群基因相近。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特色的“包容性”,可以从中华文明的国家与国民如何对待“民族”与“宗教”问题突出显现出来。中华文明“和平性”的考古学阐释,主要从“文官政治”“和亲政策”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充分反映出来。
在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中,“连续性”是历史现实,“创新性”是制度保障,“统一性”是政治要求,“包容性”包含国内包容与国外包容,“包容性”的表现形式是和平。为了弘扬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传统,继承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形成的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必须进一步深入研究其形成、发展过程及内在联系。
中华文明“连续性”就是“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的发展历史,不仅如此,而且缔造这一“文明”(中华文明)的先民与其远古的祖先也一脉相承。
中华文明“连续性”就是其国家历史发展的连续性。恩格斯提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1]的著名论断。中华文明有着五千多年不断裂的国家发展历史,中国百年考古发现与研究已经实证了五千多年以来中国国家发展史的“连续性”。从已知的秦汉帝国时代上溯至距今四千多年前的夏商周王国时代,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21世纪之初,“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出版了《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基本确认夏商周的时空[2]。其后又经多年整理、研究,编著《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报告的核心成果即夏商周编年:夏王朝:公元前2070-公元前1600年,商王朝:公元前1600-1046年,西周王朝:公元前1046-公元前771年[3]。
继“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又对与其历史源头时空追寻密切相关的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的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的“五帝时代”及其更早的“文明”遗存进行了考古学与多学科结合的科学探寻。作为“文明形成”与早期国家出现与初期发展的这一历史时期相连的“国家”之“都邑”与“帝王陵墓”类“国家文化”遗存的考古发现主要有中原地区的河南郑州5300年前的“河洛古国”城址[4]、山西临汾的距今约4300年的唐尧都邑之陶寺城址等[5-7]。出土战国时代竹简《清华简·保训篇》记载的“五帝时代”的虞舜“求中”建都于“历山”,学者研究认为“历山”即今河南“濮阳一带”[8]。与上述都邑相连的是考古发现“夏商周”的“三代”都邑,如考古发现的属于夏代早中晚期的河南登封王城岗、新密新砦、偃师二里头都邑遗址[9-14];商代的郑州商城[15-16]、偃师商城[17-18]、殷墟遗址及其西北岗商王陵[19-21]。西周的丰镐城址、周原城址与洛阳的“成周”城址[22-23]。
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古代从“王国时代”向“帝国时代”的重要转折时期,其都城与王陵的考古发现使人们看到这一历史时期的国家文化对夏商周的继承与对此后开启的帝国时代秦汉文明的影响,其相关重要考古发现与研究众多[24-27]。
中国进入“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辽金元明清的‘帝国时代’”的都城、帝王陵墓为代表的“国家文化”考古遗存的发现与研究,如秦始皇陵及秦兵马俑与秦咸阳城遗址[28]、汉长安城遗址与西汉十一陵、唐长安城遗址与唐十八陵、汉魏洛阳城遗址与洛阳北邙汉魏帝陵、隋唐洛阳城遗址、宋开封城遗址与巩义宋陵、辽上京与辽陵、金中都与金陵、元大都、明清北京城与明十三陵及清东陵与清西陵考古发现与研究等,它们充分反映了作为“国家文化”物化载体的中华民族不同族属建立的中华文明不同时期、不同王朝都城与帝王陵墓其选址、规划、布局的原则理念的“一致性”,也就是本文所说的“连续性”[29]。
中华文明“连续性”的第二个考古学实证是其“国民”一代一代的延续不断裂。从世界史来看,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国民”,像中华先民的考古发现揭示的那样:中华大地的先民历史从当今连续追溯至约百万年的人类史与一万年的文化史。
在当今中国大地考古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云南元谋上那蚌元谋人化石、陕西蓝田公王岭的“蓝田人”化石、湖北郧县百万年的人头骨与山西芮城西侯度、安徽繁昌人字洞、河北阳原泥河湾遗存。与之相连的中更新世中期(距今78万~12.8万年)在中国境内相继考古发现了北京周口店遗址、辽宁营口的金牛山遗址、辽宁本溪庙后山遗址、山西芮城匼河遗址、大荔人遗址、陕西洛南龙牙洞遗址、贵州黔西县观音洞遗址、贵州盘县大洞遗址、陕西南郑龙岗寺遗址等人类化石与文化遗存。
中国各地考古发现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存数量很多,如北京周口店、辽宁鸽子洞、河北阳原与山西阳高的泥河湾盆地、山西襄汾丁村旧石器遗址、河南郑州织机洞遗址、广东韶关马坝人遗址、广西柳江遗址等[29](P43~53+53~61+86)。
进入旧石器时代晚期,重要考古发现有北京周口店龙骨山之山顶洞遗址,遗址发现了大量人骨化石及迄今中国所知最早的墓葬。尤其是山顶洞遗址出土的人骨化石揭示,山顶洞人是原始的蒙古人种。河南新密李家沟等遗址,发现距今万年前的小型定居村落,出土了初期的陶器和细石器[30]。
与旧石器时代的“百万年人类史”直接相连接的是中华大地考古发现“一万年文化史”的缔造者留下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遗存,如新石器时代主要早期遗存:浙江浦江上山遗址[31-32]、华北地区的河北徐水南庄头、北京怀柔南庄头、门头沟东胡林、河北阳原于家沟等遗址;南方地区主要有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湖南道县玉蟾岩、广西桂林甑皮岩与庙岩、临桂大岩、广东英德牛栏洞遗址等[33](P86-109)。新石器时代主要中期遗存:裴李岗文化、大地湾文化、磁山文化、后李文化、彭头山文化、皂市下层文化、城背溪文化、跨湖桥文化、邕宁顶狮山文化等[33](P113-198)。新石器时代主要晚期文化有北方的仰韶文化及其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与南方地区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松泽文化、北阴阳营文化、薛家岗文化、凌家滩遗存等[33](P206-503)。中华文明正是这些考古学文化的先民及其后代开启的“中华文明”,并一直至今延续发展着,形成世界文明史上唯一从“百万年人类史”到“一万年文化史”发展至今的“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的中国历史。
如果说考古发现与研究实证了中华文明“连续性”,那么中华文明考古发现的出土文献与自古以来的古籍典藏又共同进一步深化、佐证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
1917年王国维依据当时可以见到的甲骨资料,撰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考证了卜辞中的先公先王之名,证明了“有商一代先公先王之名,不见于卜辞者殆鲜”。进而他得出结论:“卜辞与《世本》《史记》间毫无抵牾之处”。[34]20世纪30年代以来,殷墟甲骨出土地考古发现的宫庙建筑遗址、安阳西北岗商王陵及其殷墟遗址与其他高等级墓葬出土的青铜器、玉器及数以十几万计的甲骨,再现了3300年前中国历史上的高度文明[19]。这些考古发现、研究成果,又进一步佐证了司马迁《史记·殷本纪》是可信的。
由夏上推至“五帝时代”,作为历史文献记载的“中国通史”的“二十四史”首部《史记》开篇的《五帝本纪》,记载了中华大地的“文明”时代已经到来,中华文明形成于黄河流域中游,更为具体的空间位置,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考古发现的“大嵩山”地区的巩义河洛“古国”城址[4]、晋南襄汾陶寺城址[5-7][35-36]、登封王城岗城址[9-10]、新密新砦城址[11]、偃师二里头城址[37]、偃师商城遗址、郑州商城遗址[15]、洹北商城遗址与殷墟遗址[19]、洛邑成周遗址[29](P252)等。这些考古发现均在《史记·货殖列传》所记载的“三河”地区的“天下之中”空间范围,它们又使之将“五帝时代”与夏商周时代连在一起。
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史从《史记》到《明史》总计三千二百一十三卷、约四千万字的国家正史文献记载中得到保存并延续至今,中华文明这样的文献历史在“世界六大文明”乃至世界古代国家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此外,还有百年来震惊世界的中国考古发现的大量甲骨文、青铜器铭文与简牍、帛书、封泥等历史时期出土文献,这些考古发现与传世历史文献共同佐证了中华文明发展历史,这也是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研究中独具特色、丰富的科学资源。
关于中华文明特性之中的“创新性”,主要反映在“国家文化”的“创新性”上,而都城是国家“政治与文化之标征”[34](P451)。通过对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中的都城、帝王陵及其他相关遗迹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探索、揭示出其“创新性”内容。
(一)国家文化的物化载体——都城
都城是国家的“缩影”,我们可以从中华文明不同时期的国家都城遗址考古发现与研究提炼出都城“国家文化”的物化载体。它们在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发展史上发生着相应的“历史变化”。
1.“择中建都”政治理念的不断创新
中华文明的都城选址,体现着不同时期都城规划者的政治理念。从战国时代出土竹简记载的“五帝时代”虞舜“求中”于“鬲茅”建都[38](P143、145),学者研究认为即古文献之“历山”,属于今河南濮阳一带[39]。王国时代上甲微为大禹建都“追中”于“大嵩山”之“河”旁[39](P142-143),考古发现的“大嵩山”地区登封“王城岗城址”、新密“新砦城址”与“偃师二里头城址”,学术界一般认为它们分别属于夏王朝的早、中、晚期都城所在地[2](P86),它们与商周时代的都城郑州商城[15]-[16]、偃师商城[17][18]与殷墟及洹北商城[19]则均在当时的“天下之中”的“三河”地区①。
中华文明进入帝国时代,从秦咸阳城、汉长安城与东汉洛阳城、北魏洛阳城、隋唐长安城、宋开封城等大一统王朝的都城均在黄河流域中游的古代长安、洛阳与开封的大中原地区。
北宋王朝灭亡后,皇室南迁“临安”。海陵王顾虑开封城距金人故地黑龙江太远,不能在中原开封建都,又考虑到中华文明“择中建都”传统,于天德三年(1151)提出的“上京临潢府辟在一隅,官艰于转漕,民难于赴愬,不如都燕,以应天下之中”[40],遂建都燕京。基于这样的都城选址理念,海陵王将其都城命名“金中都”。元灭金,建立“元朝”仍然定都“北京”,并为其后的明朝与清朝所继承。
2.“宫城居中”理念的创新
考古发现的古代都城“择中建都”理念从中华文明出现伊始,一直伴随着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王国时代到来,都城布局形制又发生了更为深刻变化,即都城选址不但居中,而且在王国时代的夏代都城二里头城址的宫城又居都城遗址区中部[37],早期偃师商城的宫城亦居都城东西居中位置[41],商代中晚期的洹北商城的宫城位于其郭城的中央[42-43]。
继之到来的帝国时代,国家对于“中”的强化更为突出,帝国时代的汉长安城大朝正殿——“前殿”居宫城(未央宫)中央,此后这一制度一直延续至帝国时代结束的明清北京城。再从大朝正殿与宫城关系来看,如北魏洛阳城宫城中心的太极殿、唐长安城太极宫中央的太极殿、唐大明宫之中的中心的含元殿、隋唐洛阳城之宫城中的乾元殿、北宋东京城宫城之中的大庆殿、元大都宫城之中的大明殿、明清北京城之宫城中的奉天殿与太和殿均居各自宫城之“中心”[44]。
3.都城道路设计规划的创新
中国古代都城遗址考古发现揭示的城门、宫门及城内道路,在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发展史的不同时期也发生着重要“创新性”变化。关于都城城门、宫门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同时期其数量的多少不同,二是门道的“门洞”数量多少不一。这些都城、宫城城门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通行建筑物,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政治文化意义。因此它们不同时代的数量与形制变化,实际上是其政治上变化的“创新性”之反映。
从考古发现来看,目前古代都城四面辟门(城门)应该以偃师商城最早[41],此制一直为汉代以后中国古代都城所延续。王国时代的城门多为“单门道”。战国时代晚期的楚国都城纪南城个别城门出现“一门三道”[45-46],但是都城城门“一门三道”形成规制则始于帝国时代初期的汉长安城,其后一直延续至明清北京城[47]。其间中国历史发展鼎盛时期的唐代长安城,都城正门的明德门出现“一门五道”,与此同时大明宫正门——丹凤门亦为“一门五道”。此后,北宋开封城宫城正门宣德门、金中都宫城正门应天门、元大都宫城正门为崇天门、安徽凤阳明中都与明南京城宫城奉天门与皇城承天门之外还分别有“内五龙桥”与“外五龙桥”。明清北京城皇城正门分别为承天门与天安门,其外各置上述诸宫城与皇城城门均为“一门五道”,这些“创新性”措施无疑使国家至上、国家认同的理念越来越强化[48-53]。“五”实际上传达的是皇帝的宫城、皇城正门是以“九五之尊”的“天”之“九”与“地”之“五”。
从“王国时代”到“帝国时代”,国家通过都城道路设计规划,推出“一道三涂”的“创新性”设计规划,进一步凸显国家至上。在帝国时代初期的汉长安城与东汉洛阳城城内道路的考古勘探均已发现“一道三涂”遗迹②,并且也得到《汉书·成帝纪》的佐证,其记载就是贵为“太子”也不能跨“一道三涂”的“驰道”而行③。
(二)帝王陵墓
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上述通过都城规划、设计的思想,在强化、深化“国家”核心地位方面的“创新性”,中华文明是唯一的。涉及国家文化的不只是都城之内的各类建筑,还有都城之外的帝王陵墓,这源于中华文明的“陵墓若都邑”传统。它们至少在王国时代已经存在,如20世纪30年代著名殷墟西北岗商王陵考古发现,其墓室结构平面为“亚字形”,也就是中央为墓室,其东西南北四面各辟一门道(即墓道),门道象征性地可以通向墓外。虽然殷墟宫城的宫门尚未考古发现,至于宫城是否四面各辟一门也并不清楚,但是从已知的后代宫城四面辟门,似可推测当时宫城应该四面辟门,而宫城中部应该是主要宫庙建筑。因此国王去世之后的墓室按照宫城原理四面辟门象征面向“四方”。这种帝王陵墓的地下四墓道已知延续至西汉晚期[56]。虽然东汉及以后历代帝陵墓道变为“甲字形(即只有一个墓道)”,但是诸如北魏孝文帝长陵的陵园为夯筑城垣,四面城垣正中各辟一门,其中南门为“一门三道”形制。[57]此外,在唐宋帝陵的陵园仍然是四面辟门[58-59],这无疑应该是地下的“亚字形”墓室的四墓道变成陵园“四门道”,二者意义相同。而帝王陵墓地下“亚字形”的“四墓道”与地上都城与宫城四面辟门的意义相同,同样反映了强化“中”对“四方”(东西南北)的核心地位。这些“制度”的设计,无疑反映了对“国家认同”理念由“阳间”延伸至“阴间”,也说明中华文明随着历史发展而表现出来的国家管理理念的“创新性”。
上述都城与帝王陵墓布局形制的历史变化是随着中华文明的历史发展、国家都城“择中”理念的演进而变化,折射出中华文明国家意识不断“强化”“深化”的“创新性”。
(三)国家政治管理的创新
中华文明发展到秦汉王朝开启了帝国时代,真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形成,中央集权的多民族统一国家得以出现。正如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指出:“嬴政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以汉族为基干的民族国家,这又是一个极大重要性的历史事件,可以说是伟大中国和伟大中华民族形成的开始。”[60]与之相关国家政治管理层面的“创新”对中国乃至世界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秦王朝早在两千多年前为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巩固与发展,修建了世界上规模最长的长城、建设了从都城咸阳直达北疆的“直道”,“法令由一统”“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等[61](卷六,P239+241)。汉魏洛阳城太学遗址出土的“国家教材:熹平石经”反映中华传统文化的国家与社会“深刻思想体系”确立[62];秦汉唐宋以来古代封泥出土与研究实证了国家“郡县制”“科举制”的“独特的制度创造”[63];反映“货币官铸”的西汉都城长安锺官遗址发掘[64]、未央宫工官遗址考古发现数以6万多件的刻字骨签,再现了国家直接管理军工生产的“工官”物化载体[65];未央宫骨签遗址也成为“中国最早的中央专门档案馆库”机构设施。[66]汉代西北边疆地区的“屯田”遗存考古发现,为当今的新疆建设兵团设置找到了历史源头[67](P884)。
从中华文明“创新性”来看,中华文明“营造都市、建构和治理国家……这些重大成就展示了中华民族开拓创新、与时俱进、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是蕴含着丰富知识、智慧、艺术的无尽宝藏,是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68]。
“统一性”的核心是“统”于“一”。杜牧《阿房宫赋》:“六王毕,四海一”之“一”,就是“统一”。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历史发展中的不同“王国”及“帝国”不同“朝代”前后“延续”之“统一性”。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史的多个“王国”“王朝”,源自其国民与国家的“血缘”与“地缘”政治的“一致性”及“家国同构”的“统一性”。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生成的国家“大一统”思想,支撑着中华文明史上的国家政治发展之“连续性”历史。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历史发展中的不同“王国”“帝国”前后“延续”的“统一性”;二是“黄帝”成为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人文始祖”的统一性;三是历代对黄帝祭祀的统一性;四是帝王庙所体现“国家”治理与“国民”政治与文化思想的“统一性”。
(一)中华文明延续的“统一性”
根据翦伯赞先生主编,齐思和、刘启戈、聂崇岐先生合编的《中外历史年表》所述,公元前4500~公元前2560年为传说时代,从公元前2550年开启人类社会的“历史时代”,这也是黄帝出现的年代[69]。《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确定的夏代编年为公元前2070~1600年[3]。从黄帝的公元前2550年至公元前2070年应该就是《史记·五帝本纪》的“五帝时代”。
“黄帝”在东自山东、西至陇西,南由湖南、北到河北涿鹿之间征战,在这一范围的中心地区——黄河流域中游创建了“有熊国”,标志着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形成,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的“国家”时代到来[61](卷一)。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佐证了司马迁《史记》中“五帝”时代的存在以及与“文明要素”相关的记载,包括与“仓颉造字”有关的刻划文字、“黄帝铸鼎”的金属器。黄河流域中游诞生的夏商周(成周)王国,围绕在“大嵩山”地区的周围,也就是司马迁《史记》中所说的“天地之中”④,中华文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其中4200年的中心就在这里。
(二)黄帝——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统一的“人文始祖”
黄帝作为“人文始祖”,从血缘政治上说黄帝是中华民族的“祖宗”,从中华文明的地缘政治上说他是中国的“国父”,而不是中国历史某个王国、或王朝的国王或皇帝,如大禹、商汤、周武王、秦始皇、汉高祖等,后者只是其各自王国、王朝的“国父”。中华文明“统一性”首先是反映在通过对“中华文明共同”“祖先”“与“国父”黄帝的祭祀体现出来,并一代又一代传承。
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主体”是创造者的“不断裂”。中国考古百年的发现与体质人类学、分子生物学、姓氏学等多学科研究结果显示,目前中国本土的绝大部分人的基因与五六千年前的黄河流域中游地区人群基因相近[70]。近年来考古学、分子人类学的进一步深入研究表明,“在距今5000-6000年,华夏族从汉藏语系群体中分化出来集居在黄河中上游盆地,这就是汉族前身”[71]。
五千多年来对于中华“人文始祖”的“年复一年”的“不断裂”的祭祀,反映了中国人五千年多来对华夏的“大一统”国家认同,这些“认同者”不限于“中原”地区,历史上的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四夷”人群亦然[61](卷一,P28)。在这广阔的中华文明大地,四方之人群有着共同的“祖宗”——“黄帝”。属于“东夷”的“少昊”族群,历史文献记载少昊为“黄帝之子”⑤。起家于西戎之地的秦人,自称“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61](卷五,P173)“西戎”的后人苻洪(前秦皇帝)自称其祖先为“有扈之苗裔,世为西戎酋长”[72](卷一百一十二,P2867)。“有扈”为大禹之后[60](卷二,P89)。后秦皇帝姚苌,自认为其祖先“羌酋”是虞舜之后⑥。《史记·楚世家》记载南蛮的楚人其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60](卷四十,P1698)。《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载南蛮的另一支“百越”,其先祖属于“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60](卷四十一,P1739)。北方地区的匈奴自称:“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60](卷一百一十,P2879)《山海经·海经》则明确指出:“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于北狄。”[73](P395)
北魏鲜卑人自称:“魏之先,出自黄帝轩辕氏。黄帝之子曰昌意,昌意之少子受封北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74](卷一,P1)北燕开国皇帝惠懿帝高云自认其是高句丽之支庶,出自黄帝之孙高阳氏颛顼[72](卷一百二十四,P3108)。中古时代及以后建立辽、元王朝的契丹、蒙古(蒙兀室韦)族群,他们均源于汉代的鲜卑[75](P256-260+P289-295)。
金朝为女真人所建,女真可溯源于商周之际东北地区的“肃慎”[76](P7),汉晋至隋唐先后称“挹娄”“勿吉”“黑水靺鞨”,辽称“女真”。主要活动区域在黑龙江镜泊湖地区、吉林松花江中上游的吉林市与永吉县之间,考古发现的距今3000年左右的莺歌岭文化与西团山文化,学术界一般认为它们属于历史记载的“肃慎”族群的考古遗存。西团山文化遗存中的鼎、鬲、甑等陶器与中原地区同时代的同样陶器基本相同。这就说明三千年前的东北地区的“肃慎”考古学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密切关系。史载金宣宗贞祐四年(1216),参议官王浍与金朝女真贵族完颜海奴谈到,“本朝绍高辛,黄帝之后也”[77](P265)。关于建立清王朝的女真,以后又称满族,其与大金王朝的女真是同一民族,《清史稿·太祖纪》载:“其先盖金遗部。”[78](卷一,P1)
近年来“姓氏学”在历史研究中提出不少新的观点,这是因为就世界而言,欧洲人使用“姓”只有400年历史;日本人在明治维新时期才开始出现“姓”;人类文明最早起源地的西亚土耳其,直到1935年才以法律规定使用姓。而中华文明的“姓”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产生[79]。据统计,在“当今中国流行的前200个姓氏中,出自炎帝姜姓系统的姓氏约占10%,出自黄帝姬姓系统的姓氏约占89%”。也就是说当今中国人应有99%为“炎黄子孙”[80]。从血缘系统看,现代中国人的先民是来自中国这片古老土地上的百万年、一万年、五千年的我们的先人。这是中华文明统一性的“血缘”基础。就“地缘”而言,“黄帝”不只是中国的“国父”,更是中国的“第一国父”[81]。
在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发展中,包括了不同时期、不同族群建立的大大小小许多“王国”“朝代”,但是“黄帝”一直被不同时期、中华民族不同族属人们所建立的不同“王国”“朝代”统治者视为“祖先”与“国父”双重身份进行祭祀。关于古代国家“祭祖”的内涵,不是一家一户一族的“血缘祭祀”,而是国家的“政治祭祀”,所谓“政治祭祀”就是祭祀“人文始祖”的“国父”与国民“祖宗”。这就是在世界文明史中唯独中华文明存在的“统一性”特色,而这一意识的形成与发展是造就中华不断裂文明的“思想基础”。因为上古时代至今的中国不是西方的“城邦国家”或曰“民族国家”,中国历史显示其国家从形成伊始就是跨地域、多族群的国家。
(三)黄帝祭祀
《左传·成公十三年》记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被列为国家大事,祭祀的主体自然是“国家”。在中华文明的国家祭祀中,只有“黄帝”具有中国人的“祖宗”与国家缔造者“帝王”双重身份。因此黄帝被称为中华文明的“人文始祖”。这是维系五千多年文明发展的国家“统一性”之重要基础。
国家祭祀黄帝有着久远历史,《竹书纪年》记载:“黄帝仙去,其臣有左彻者,削木作黄帝之像,帅诸侯奉之。”《国语·鲁语》记载:“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三代祭祀黄帝属于“国之典祀”。
进入秦汉时代,国家对黄帝祭祀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史记·秦本纪》记载秦灵公在秦国都城雍城(今凤翔)附近祭祀黄帝⑦。这已被近年来考古发现所证实,在陕西省凤翔县西北柳林镇的血池村,考古发现了一处面积470万平方米秦汉时代祭祀遗址,已考古发现3200个祭祀坑,坑里面发现了大量的马骨、木车、金属残片和玉器。根据已发掘面积,推测该处至少有祭祀坑约有5000个。祭祀坑中发现了大量的马骨、木车、金属残片和玉器。在祭祀坑附近山梁上发现了夯土祭坛,发掘者认为,该遗址与祭祀“黄帝”有关[82]。秦汉时代对黄帝的祭祀,以汉武帝在桥山祭祀黄帝陵影响较大⑧。
魏晋南北朝与宋辽金元两个历史时期,是多民族统一国家重大发展与“转型”时期,北方少数族群进入中原,并相继建立由少数族群按照传统中华文化构建的中华帝国,如鲜卑人建立的北魏王朝、党项建立的西夏、契丹人建立的辽王朝、女贞(黑水女贞)建立金王朝、蒙古建立的元王朝等。国家祭祀黄帝的传统被继承下来,如公元415年北魏明元帝在桥山“以太牢祠黄帝”[74](卷一,P34)。祭祀成为重要的“国家行为”。
作为国家统治者,都将祭祀黄帝视为国家的重大祭祀活动,这是中华文明特性之“统一性”与中华文明密不可分的根本原因。这体现了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的“统一性”成为亘古不变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四)帝王庙
在中古时代以后的中国古代都城出现的帝王庙,是祭祀传说时代“帝王”与“前朝”帝王及有“文治武功”名臣的建筑,也可以说“帝王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国家历史博物馆”。唐天宝年间,唐玄宗在唐长安城分别建帝王庙,祭祀三皇、五帝及周武王、汉高祖。与此同时还在上述帝王故地置庙祭祀。
明清两代南京城与北京城的帝王庙已经发展为“中国”的国家“宗庙”,成为多民族统一国家完整历史的缩影。
明代朱元璋在明中都与明南京城先后营建了历代帝王庙。洪武六年(1373),朱元璋在都城南京钦天山建历代帝王庙。建帝王庙之初,朱元璋明确提出帝王庙中祭祀“重一统”“统一天下”的开创之主,进入帝王庙的是黄帝等“五帝”及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汉高祖、光武帝、唐高祖、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等十八位夏商周汉唐宋元王朝的开国君主。其中将元代皇帝置于帝王庙中,标志着元王朝被明代承认为正统王朝。明代把以前的“帝王庙”发展为“历代帝王庙”,“历代”至关重要,这是跨越“朝代”的“国家历史”。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朱元璋又增加三十七位夏商周汉唐宋元王朝的“名臣”从祠于历代帝王庙[83](卷五十,P1293),这些名臣之中有汉族,也有少数民族。至此,明代形成了三皇五帝与创业帝王、功臣体系的帝王庙祭祀制度。永乐徙都北京之后,明世宗嘉靖九年(1530)“建历代帝王庙于都城西”。
清代北京城历代帝王庙沿袭了明代北京城历代帝王庙,其最大特点是一些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帝王进入历代帝王庙祭祀对象之中,如辽、金、元三代帝王及其名臣,还有明代的国君与功臣。清代的“历代帝王庙”的祭祀对象包括了中国古代历史上几乎所有王朝与绝大多数帝王,其祭祀内容发展到“全面”“系统”“完整”的对以历代王朝君主为代表的“国家”祭祀,历代帝王庙真正成为“国家”的“庙”,而不是某个王国、王朝的“庙”、某个“圣君”的“庙”。“帝王庙”维系“中华统绪”,体现的是“国家”的“大一统”“统一性”历史,历代帝王庙成为多民族统一国家完整历史的缩影。作为王朝更替时期的“偏安”的“流亡政府”及其“帝王”一概不能入祀“帝王庙”,比如,顺治十四年涉及入祀帝王庙皇帝人选,辽太祖、金太祖、元太祖就因为他们在位时,国家还没有“统一”,就不能入帝王庙享祭。乾隆皇帝对于帝王入祀帝王庙,要体现“中华统绪,不绝如线。”这里将“统一”与“连续”连接一起,并作为“帝王庙”的主旨。这充分体现出“帝王庙”的国家“正统”理念之下的“统一性”、原则性。
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在“帝王庙”中反映出来的多民族的中华文明形成的国家的“统一”原则。这个“统一性”就是帝王庙他们尊重的是国家的“统一”与“国民”的“统一”,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形成并发展的文明史,不论在这条历史长河中哪个王朝、哪个民族作为国家统治者,历代帝王庙体现出的都是视其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有机组成部分,都是中华民族历史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被外国学者倍加推崇,英国学者汤因比认为:“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84](P294)
(一)对内“包容性”
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特色的“包容性”,可以从中华文明的国家与国民如何对待“民族”与“宗教”问题突出显现出来。就古代中国历史而言,中国是多民族组成的国家,有着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史,国土面积之大、国民不同族群之多,在世界上是十分突出的。但是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历史包括数十个王朝,其国王或皇帝并不都是由某一个民族的政治人物。如刘邦是汉王朝的皇帝,北魏王朝皇帝就是少数族群的鲜卑人,元王朝皇帝是蒙古族,金朝皇帝是女贞族,清王朝皇帝是满族人,等等。周秦汉唐宋明等王朝的皇帝虽然是汉族人,但是其中央政府的不少重要官员是少数民族,如被汉武帝拜为马监,迁侍中驸马都尉光禄大夫的金日磾,其父为匈奴休屠王,后降汉入官,输黄门养马。《汉书》称誉:“金日磾夷狄亡国,羁虏汉庭,而以笃敬吾主,忠信自著,勒功上将,传国后祠,世名忠孝,七世内侍,何其盛也!”[55](卷六十八,P2967)有唐一代,在都城长安有不少各民族的酋长与外国政治家、军事家供职于唐朝中央政府,并身居要职,长期留居长安。唐王朝的少数民族中,以突厥、吐蕃、于阗、疏勒、靺鞨、鲜卑人供职唐朝中央政府的较多,如右卫大将军史达奈、突厥可汗之子阿史那社尔因成为皇室驸马并任鸿胪卿与左卫大将军,死后并陪葬昭陵,昭陵祭坛上著名的十四蕃酋像就有阿史那社尔的石像。
中华民族的第二个大发展与大融合的历史时期,是中古时代后期的西夏、辽、金、元、清王朝时期,以上王朝的统治者均出身于中原地区以外的中华民族少数族群。但是这些王朝的都城、帝陵选址及其建筑布局形制与相关遗存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充分揭示了他们的核心政治理念对中华文明认同。这恰好反映了多民族组成的统一国家的包容性,这是中华文明不断裂的内部凝聚力的文化基因使然,正如英国学者罗素所说:“中国人的实力在于四万万人口,在于民族习惯的坚韧不拔,在于强大的消极抵抗力,以及无可伦比的民族凝聚力。”[85](P165)
(二)对外“包容性”
中华文明发展中对外的“包容性”主要表现在域外宗教在中国的发展与中华文明开创的丝绸之路对世界文化交流的贡献两方面。
首先,域外宗教在中国的发展实证了中华文明发展道路的“包容性”。中华文明在世界古代史上的一个重要特色是其“包容性”显示出的开放性,对此可以从历史上域外宗教在中国的活动得到充分反映。早在两千多年前,西汉王朝开通了连接世界东西方的丝绸之路,此后汉唐宋元时代,这里活跃着世界历史上著名的琐罗亚斯德教(中国古代称祆教、拜火教)、佛教、摩尼教、景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道教六大宗教。它们大多集中于国家都城附近,这些宗教与本土宗教(道教)在中华大地不只是平等发展,而且有的比道教还要更受重视,其中尤以佛教从域外传入中国后的发展最为典型。
在长安为官供职唐王朝政府有大量的波斯、大食、天竺、日本、高丽及西域诸国人士。西安地区考古发现的三彩骆驼载物俑、西安南何村出土的唐三彩骆驼载乐俑(乐俑)、西安南郊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东罗马和阿拉伯人铸造的拜占庭金币、阿拉伯金币[86](P165)。这些应该是通过丝绸之路来到唐长安城进行商贸活动流行的遗物,见证了中华文明的政治、文化、经济等方方面面的“包容性”。汉唐时代中华民族历史上的那样“包容性”是十分难得的!
(一)文官政治
中国古代的官制发展历史,丞相与将军前者为上,这保证了国家政治的稳定性、连续性与国家“贤明政治”共同构成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和平性”特色。中华文明在这些领域的政治与组织措施,保证了国家历史发展相对更为和平、平稳与持久。这从历史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两个方面可以得到佐证。
从中央政府的皇帝之下的官员,以“文官”的“丞相”地位最高,《汉书·百官公卿表》卷十九载:“相国、丞相,皆秦官,金印紫绶,掌丞天子助理万机。”汉武帝以前,丞相多功臣出身,位极尊隆,总领百官,管辖一切国事。在帝王陵的“陪葬墓”中,陪葬墓在帝王陵墓陪葬区的位置,一般折射出其生前地位之“高低”。汉高祖刘邦长陵的陪葬墓区在长陵之东,距帝陵最近的陪葬墓是丞相萧何与曹参[56];又如,唐太宗昭陵,距其帝陵最近的陪葬墓是丞相魏征墓[58]。
(二)和亲政策
作为由多地区、多民族组成的真正“广域”国家,中国历史上的“和亲”活动具有“中华文明”的“和平性”特色。正如在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史发展史中,由多民族组成的“民族共同体”如何实现的,是世界历史上长时间未能处理好的难题。但是中华文明的“和平性”在处理中华民族共同体关系上,早在两千多年前实施的“和亲”活动充分体现出中华文明的“和平性”特点。
汉朝政府为巩固、发展与邻近国家和地区的友好关系,往往采取和亲政策。所谓和亲,就是汉朝把宗室的女儿或宫女嫁给那些地区的酋长与首领。这些女子作为和亲的使者,为巩固和发展所在地区与汉王朝的友好关系、增进民族融合与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其中不少人成了名垂青史的政治活动家。如江都王刘建的女儿细君,汉武帝于元封六年(前105)把她作为公主嫁给了乌孙国王昆莫,细君到达乌孙后,积极开展外交活动,把从长安带去的华丽丝绸等贵重物品,赠送给乌孙的达官显贵们。细君病逝,汉武帝又将解忧公主嫁给乌孙国王,她在西域乌孙生活了五十多年,加强西汉王朝与西域友好与亲情关系,加强了乌孙与汉朝的友好关系[55](卷九十六)。西汉一代和亲政策影响最大的历史事件,莫过于昭君出塞,曾使中国北部的和平安定持续了半个多世纪[55](卷九十四)。
(三)丝绸之路“和为贵”的特征
公元前114年,以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调查、了解西域“大国”乌孙情况,并力图加强双方联系,并向乌孙国王提出“妻以公主,与为昆弟”,皇室“细君公主”嫁给乌孙国王[55](卷九十六(下))。开启了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所称的“丝绸之路”,它早于大航海时代1600多年。丝绸之路是中国境内各民族的和合之路,也是世界古代史上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在“和合”理念之下的文化交流活动之路。
西方地理学家称誉大航海是人类的地理大发现,是世界史上的辉煌。历史发展的事实告诉人们,大航海带给世界史的是殖民时代!留下的历史是随之而来的殖民掠夺、非洲黑奴贩运,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许多国家,从此逐渐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残酷的殖民掠夺,给这些地区的人民带来巨大灾难。与西方大航海历史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两千多年前中华文明开创的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这是汉唐盛世中华民族的发展之路、强大之路,是中国走向世界之路,也是世界走向中国之路!是中国与世界的“和平之路”!
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是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诸多元素共同塑造出来的。“连续性”是“时间”,也就是“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时间的长久意味着其历史“科学性”越强。“历史”之“时间”的发展,必须以“创新性”适应社会发展规律。国家的“统一性”、大政方针的“包容性”与“和平性”是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总结出来的成功历史规律和“经验”。
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史的“连续性”是基于其历史发展中的“创新性”,历史发展如果缺乏“创新性”也就失去了其“生命力”。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史的“连续性”形成、发展与中华文明不断的“创新性”密切相关。中华文明五千多年不断裂发展史,由于其时空、人群(国民)构成、社会经济发展进程等不同,经历了从“文明形成”初期的“古国时代”到“王国时代”,再至直接影响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帝国时代”。“统一性”带来的是中华文明的“盛世”。在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发展史上,凡是国家从“分裂”走向统一的时期,都是国家历史的“盛世”。王国时代“大一统”的西周王朝走向“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春秋战国时代,秦汉开创了“大一统”的中华文明,建立了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文景之治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盛世。东汉末年国家出现魏蜀吴分裂局面,继之又造成了魏晋南北朝全国大分裂局面。隋唐盛世结束了国家分裂,国家形成空前的统一,开创了大唐盛世,造就出中华文明历史上的“黄金时代”。
“连续性”的形成离不开“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而后四者一而贯之,使得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的“文化基因”发挥着持之以恒的历史作用。通过考古学遗存的发现与研究,我们揭示出,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的“文化基因”,它就是从“家国一体”[87]到“国家认同”[88](P419-423)。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与中华文明发展史是同步“前行”的。
注释:
①《史记·货殖列传》:“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
②《太平御览》引《洛阳记》:“宫门及城中大道皆分作三,中央御道,两旁筑土墙高四余尺,外分之唯公卿尚书章服从中道,凡行人皆左右。”
③《汉书·成帝纪》:“元帝即位,帝(汉成帝)为太子。壮好经书,宽博谨慎,初居桂宫,上尝急召,太子初出龙楼门,不敢绝驰道,西至直城门,得绝乃度,还入作室门。”
④《史记·货殖列传》:“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
⑤《史记·五帝本纪》:“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索隐案:“皇甫谧以青阳为少昊。”
⑥《晋书·姚弋仲载记》:“禹封舜少子于西戎,世为羌首。
⑦《汉书·郊祀志(上)》:“秦灵公于吴阳作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
⑧《史记·封禅书》:“其来年冬,上议曰:‘古者先振兵泽旅,然后封禅。’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余万,还祭黄帝冢桥山,释兵须如。上曰:吾闻黄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对曰:‘黄帝已僊上天,群臣葬其衣冠。’”。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
[3]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22.
[4]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巩义市双槐树新石器时代遗址[J].考古,2021(7):27-48.
[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山西襄汾陶寺城址2002年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2005(3):307-346.
[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山西襄汾县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中期大型夯土建筑基址[J].考古,2008(3):3-6.
[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III区大型夯土基址发掘简报[J].考古,2015(1):30-39.
[8]冯时.《保训》故事与地中之变迁[J].考古学报,2015(2):129-156.
[9]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登封王城岗与阳城[M].北京:文物出版社,1962.
[10]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登封王城岗考古发现与研究(2002~2005)[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7.
[11]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新密新砦——1999~2000年田野考古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
[1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1999~2006)[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
[13]赵海涛.二里头都邑聚落形态新识[J].考古,2020(8):109-120.
[1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中心区2019~2020年发掘收获[A].国家文物局.2020中国重要考古发现[M].北京:文物出版社,2021.
[15]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
[16]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考古新发现与研究:1985-1992[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
[17]杜金鹏,王学荣.偃师商城遗址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1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商城(第一卷)[M].科学出版社,2013.
[1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
[2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2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洹北商城的勘察与试掘[J].考古,2003(5):3-16.
[2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丰镐考古八十年[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
[2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两周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2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报告(1955~1960年洛阳涧滨考古发掘资料)[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
[25]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晋都新田[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
[26]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等.赵都邯郸故城调查报告[A].《考古》编辑部.考古学集刊(四)[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27]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邯郸赵王陵[J].考古,1982(6):597-605+564.
[28]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都咸阳考古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29]刘庆柱主编.中国考古发现与研究(1949-2009)[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30]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新密李家沟遗址南区2010年发掘简报[J].中原文物,2018(6):38-45.
[31]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浦江博物馆.浙江浦江县上山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2007(9):7-18.
[32]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浦江博物馆.浦江上山:浦阳江流域考古报告之三[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
[3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34]王国维.观堂集林(二)[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山西襄汾县陶寺城址祭祀区大型建筑基址2003年发掘简报[J].考古,2004(7):9-24.
[3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山西襄汾县陶寺中期城址大型建筑IIFJT1基址2004~2005年发掘简报[J].考古,2007(4):3-25.
[3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1955-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
[38]李学勤.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M].上海:中西书局,2010.
[39]冯时.文明以止:上古的天文、思想与制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40][元]孛兰肹.元一统志[M].北京:中华书局,1966.
[41]王学荣.河南偃师商城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求知集:考古研究所中青年学术讨论会文集[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4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洹北商城宫殿区1号基址发掘简报[J].考古,2003(5):17-23.
[4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洹北商城宫殿区二号基址发掘简报[J].考古,2010(1):9-22.
[44]刘庆柱.中国古代宫城考古学研究的几个问题[J].文物,1998(3):49-57.
[45]湖北省博物馆.楚都纪南城的勘察与发掘(上)[J].考古学报,1982(3):325-349.
[46]湖北省博物馆.楚都纪南城的勘察与发掘(下)[J].考古学报,1982(4):477-506.
[47]刘庆柱.汉长安城的考古发现及相关问题研究[J].考古,1996(10):1-14.
[48]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工作队.唐代长安城明德门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1974(1):33-39.
[4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队.西安市唐长安城大明宫丹凤门遗址的发掘[J].考古,2006(7).
[50]傅熹年.傅熹年建筑史论文集[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51]北京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西厢道路工程考古发掘简报[A].北京文物与考古(第四辑)[C].北京:北京文物考古研究所,1994.
[52]傅熹年.元大都大内宫殿的复原研究[J].考古学报,1993(1):109-151.
[53]刘庆柱.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研究的几个问题[J].考古,2000(7):60-69.
[54][宋]李昉等,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1960.
[55][东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56]刘庆柱,李毓芳.西汉十一陵[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
[57]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北魏孝文帝长陵的调查与钻探[J].文物,2005(7):50-62.
[58]刘庆柱,李毓芳.陕西唐陵调查报告[A].《考古》编辑部.考古学集刊(五)[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59]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宋皇陵[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
[60]范文澜.中华民族的发展[J].学习,1950(1):45-49.
[61][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6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魏洛阳故城南郊礼制建筑遗址:1962~1992年考古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
[63]孙慰祖.中国古代封泥全集[M].长春:吉林美术出版社,2022.
[64]西安市文物保护修复中心.汉钟官铸钱遗址[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6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未央宫骨签[M].北京:中华书局,2018.
[66]刘国能.我国最早的中央专门档案馆库的发现——汉代骨签档案馆库[N].人民政协报,2007-10-11(B1).
[6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秦汉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68]习近平.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J].求是,2020(23):4-9.
[69]翦伯赞,齐思和,刘启戈,等.中外历史年表[M].北京:中华书局,1962.
[70]金力,李辉,文波,等.遗传学证实汉文化的扩散源于人口扩张[J].自然,2004(431):302-304.
[71]李辉,金力.Y染色体与东亚族群演化[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
[72][唐]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73]袁珂.山海经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74][唐]李延寿.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75]高凯军.论中华民族——从地域特点和长城的兴废看中华民族的起源形成与发展[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
[76]张博良,魏存成.东北古代民族考古与疆域[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
[77]张广智.大嵩山:华夏历史文明核心的文化解读[M].郑州:大象出版社,2016.
[78]赵尔巽,缪荃孙,柯邵忞,等.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6.
[79]袁义达,张诚.中国姓氏:群体遗传和人口分布[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80]刘文学.建设华人寻根圣地传承华夏历史文明[A].张新斌,刘五一.黄帝与中华姓氏[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3.
[81]刘庆柱.国祭也是祭国[N].光明日报,2015-09-07(16).
[82]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凤翔雍山血池秦汉祭祀遗址考古调查与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20(6):3-24.
[83][清]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84][英]阿诺德·汤因比,[日]池田大作.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
[85]罗素.中国问题[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
[86]刘庆柱.地下长安[M].北京:中华书局,2016.
[87]刘庆柱.中与中和的考古学阐释[N].光明日报,2021-01-13(11).
[88]刘庆柱.不断裂的文明史:对中国国家认同的五千年考古学解读[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
作者:刘庆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郑州大学特聘教授,德国考古研究院通讯院士)
文章原载于《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 第1期
文章来源:郑大学报哲社版 公众号 链接: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考古学阐释